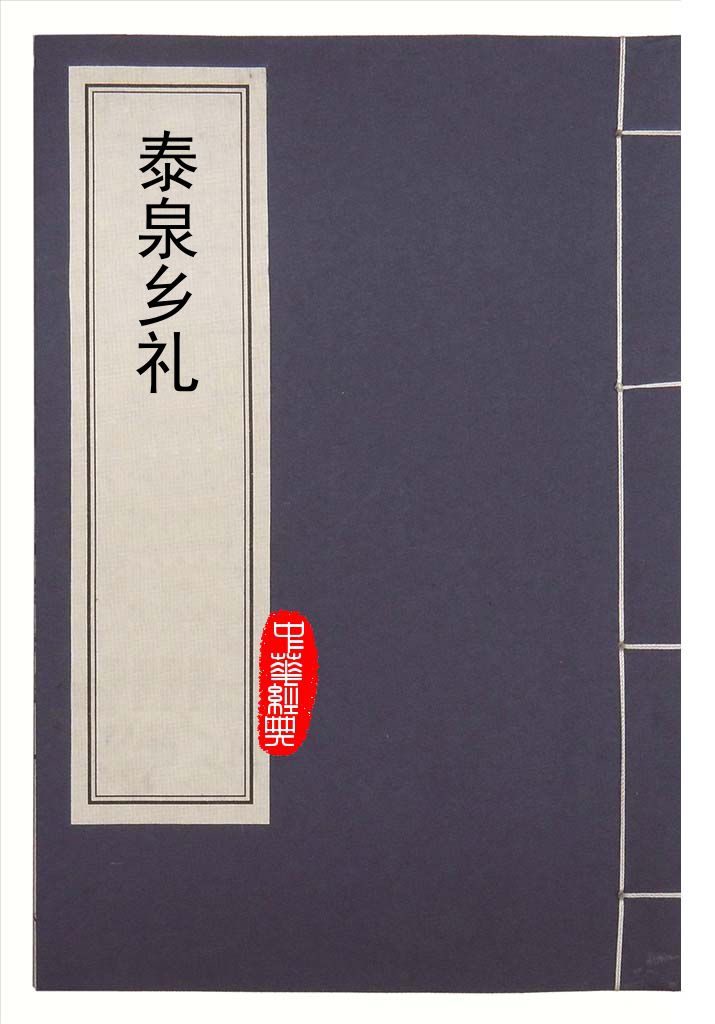
《泰泉乡礼》七卷,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于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4.01 万字 | 2019-04-05 15:09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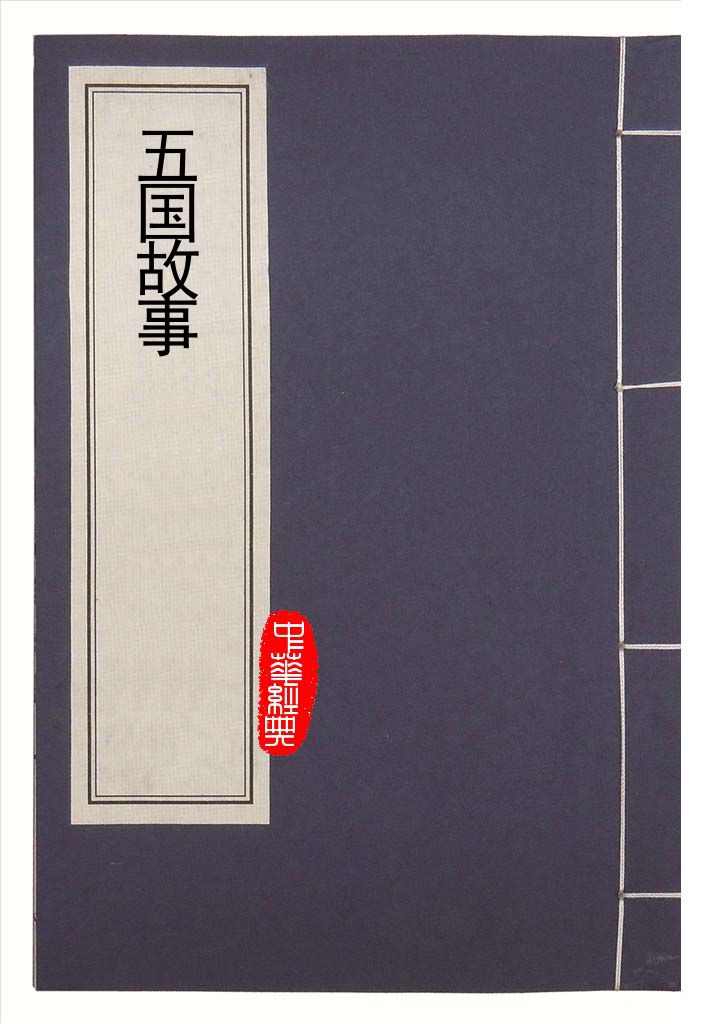
五国故事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南汉”条下称刘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讳,去之,则北宋人。又“南唐”条下称尝以其事质於江南一朝士,则犹在宋初,得见李氏旧臣也。中於南汉称彭城氏,於留从效姓称娄。钱塘厉鹗跋,以为吴越国人入宋所作,避武肃王讳。然闽王“延翰”条下,称其妻为博陵氏,则又何为而讳崔乎?年代绵邈,盖不可考矣。其书纪吴杨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之事,称曰五国。然以其地而论,当为四国。若以其人而论,当为六国。未审其杨、李并为一,抑孟、王并为一也。郑樵《通志略》列之《霸史类》中,实则小说之体,记录颇为繁碎。中如徐知诰斥进黄袍诸事,为史所不载。又李煜为李璟第六子,而此云璟之次子,与史亦小有异同。然考古在於博徵,固未可以琐杂废也。前有万历中太常寺少卿余寅题词,讥其四国俱加伪字,於蜀独否。今考书中明书伪蜀王建,又书孟知祥以长兴五年遂僣大号,何尝不著其伪。卷首总纲既以前蜀、後蜀为分,再加伪字,则或曰前伪蜀、後伪蜀,或曰伪前蜀、伪後蜀,词句皆嫌於赘,是以省之。《公羊传》所谓避不成文是也。谓不伪蜀,殊失其旨。至“南汉”条下称伪汉先主名岩,後名俊,又名,之字曰俨,本无此字,欲自大,乃以龙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书之。寅援《唐史》书武后名曌以驳之,则其说当矣。出《四库总目提要》
1.08 万字 | 2019-04-06 22:47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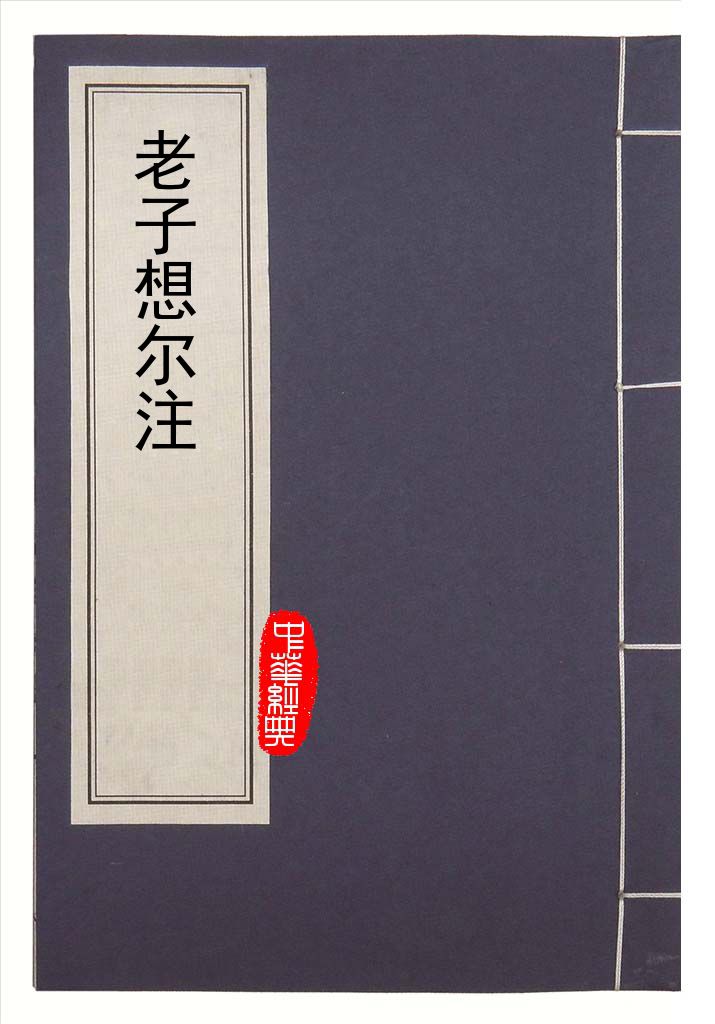
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以《道经》为后,创五斗米道,将老子奉为“太上老君”,为道教教祖,是为早期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是早期道教的主要著作,一名《老君道德经想尔训》。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以《五千文》为主要经典,《想尔注》便是米道祭酒宣讲《老子》的注释本,此书早佚。清末於敦煌莫高窟发现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现藏大英博物馆。此书作者,或说张道陵,或说张鲁,或说「想尔」为仙人名。其内容多与《太平经》相合,吸取了後者的宗教思想与社会政治观,也有河上公解释《老子》的观点,是研究五斗米道最原始、最宝贵的材料。
1.31 万字 | 2019-04-07 16:01更新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487.11 万字 | 2019-04-05 15:52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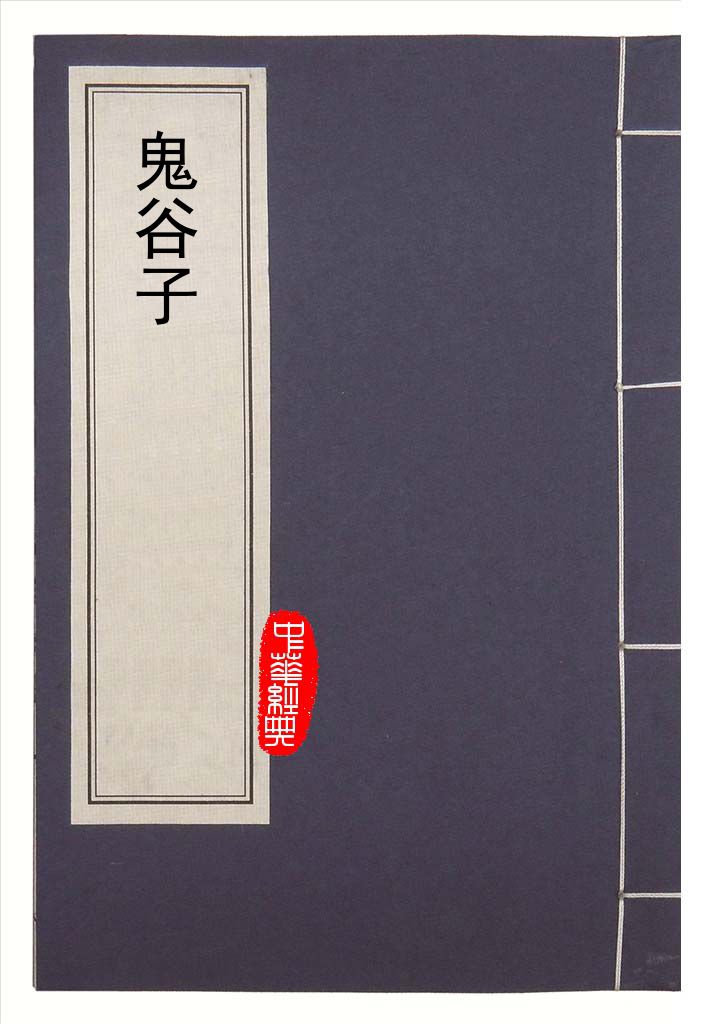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 《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此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0.82 万字 | 2019-04-07 21:16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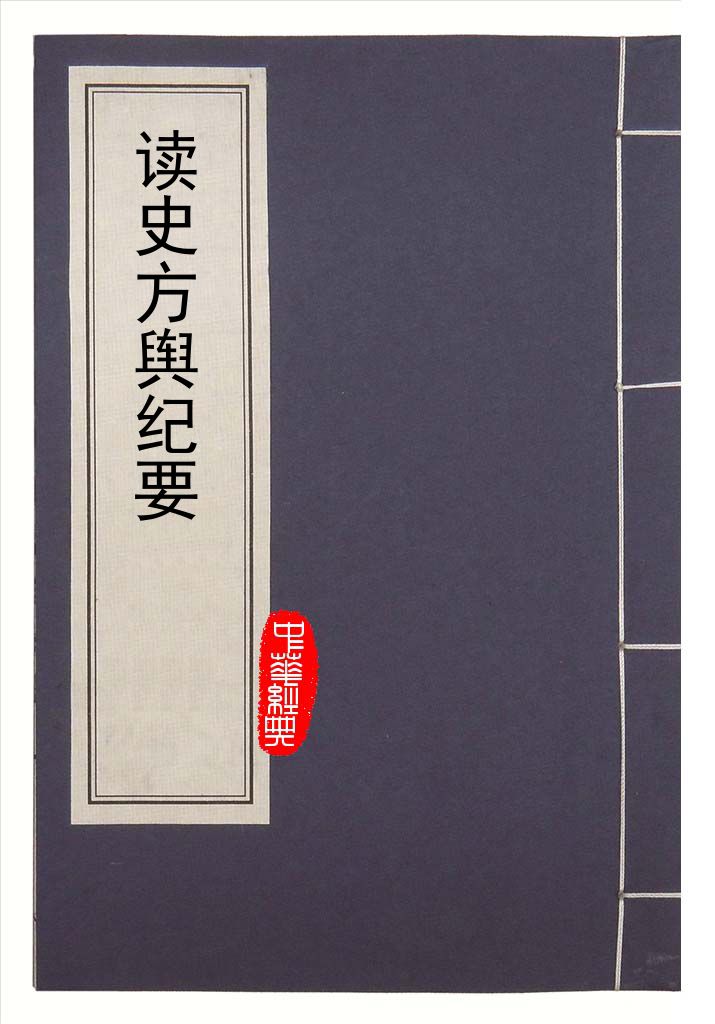
"千古绝作","海内奇书"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279.00 万字 | 2019-04-06 23:14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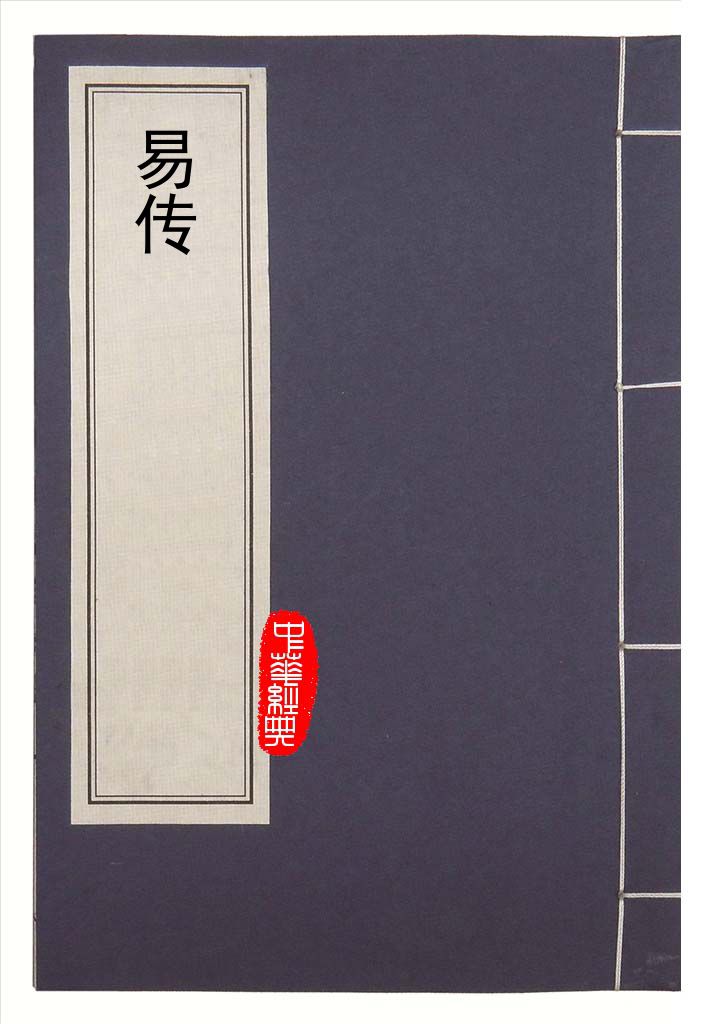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易传》共7种10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角、《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4种,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7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4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优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家,四家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0.97 万字 | 2019-04-05 15:10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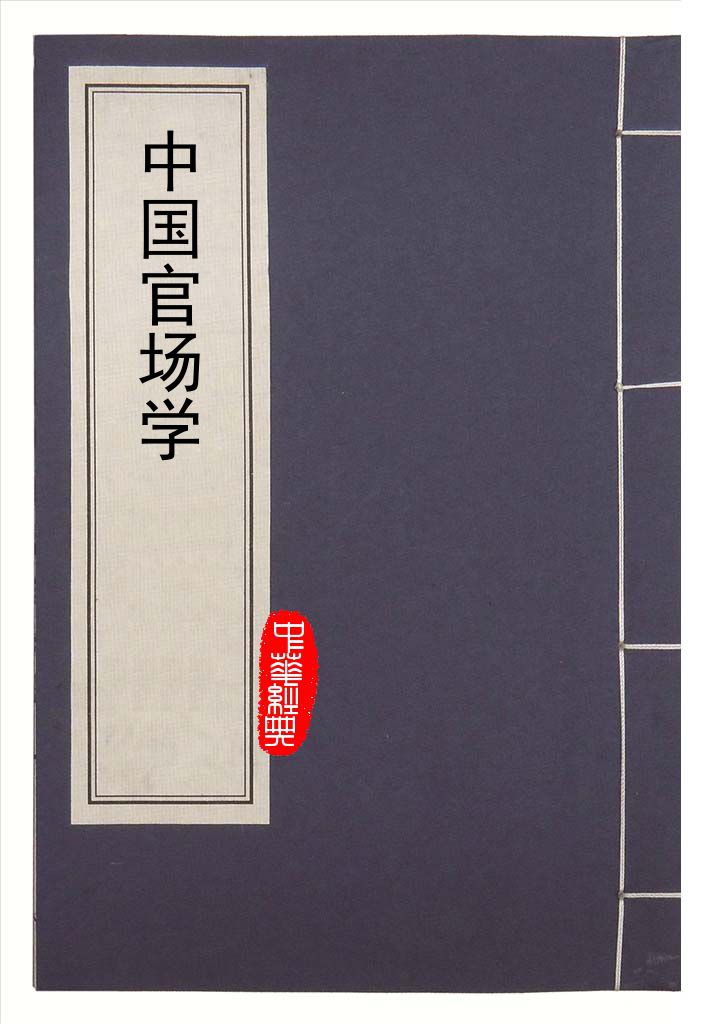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5.16 万字 | 2019-04-07 13:44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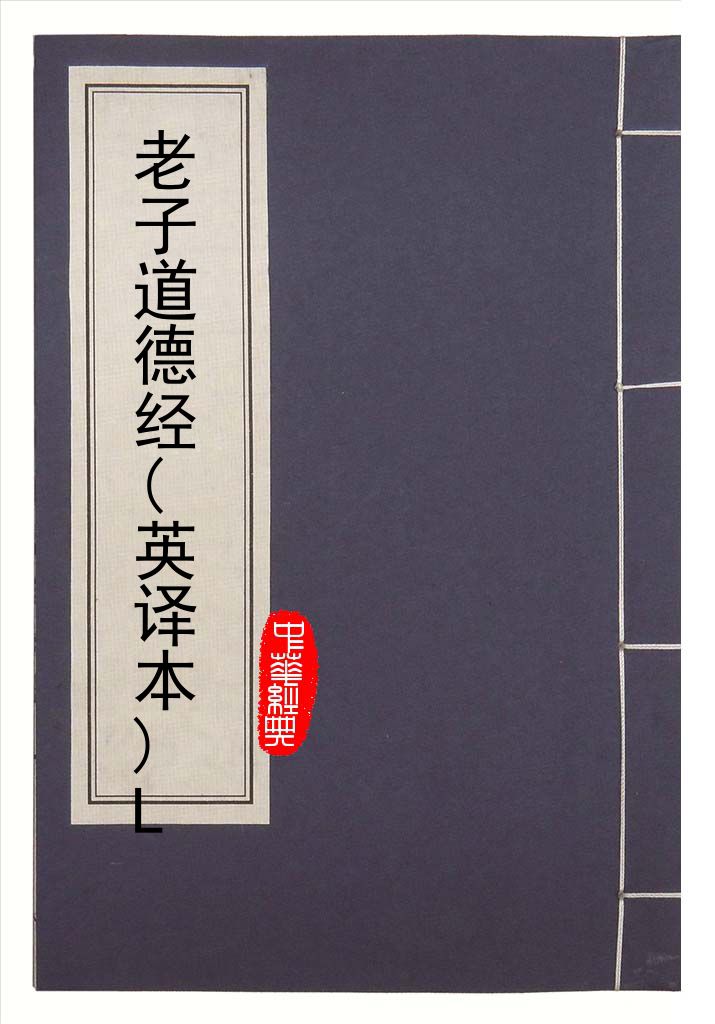
Lao TzeThe full text of TaoDeJing consisting of 81 Chapters can be browsed chapter-by-chapter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To see a particular chapter, just click on the Chapter Number to go there directly. While positioned at any chapter, you may switch to the Chinese text of that chpater. And back.
3.98 万字 | 2019-04-07 18:48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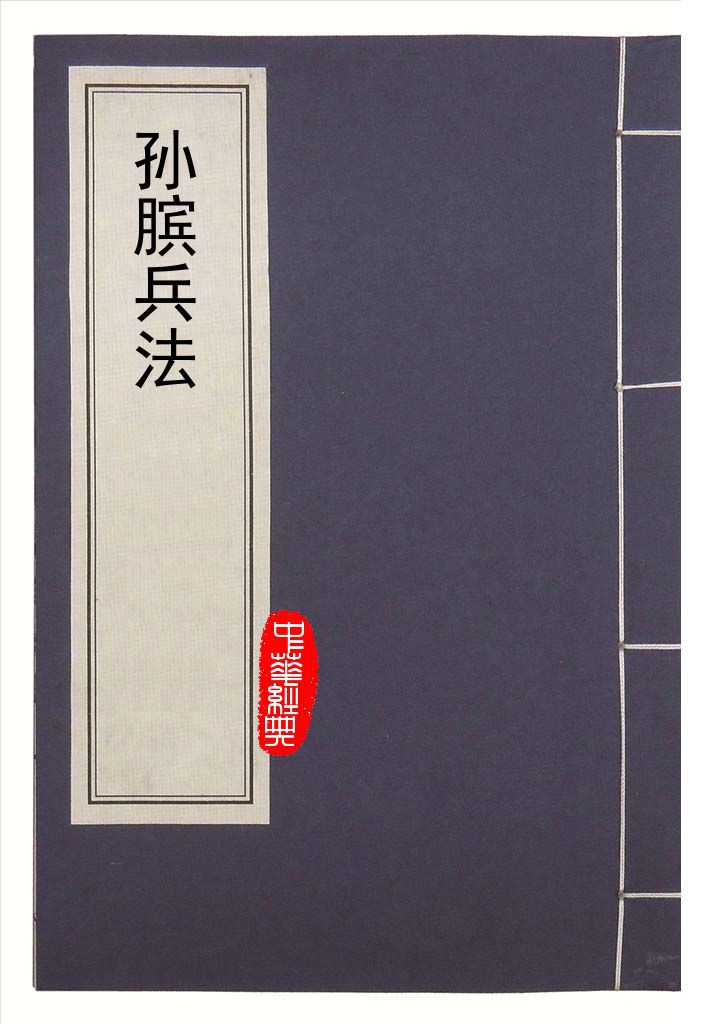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后来,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设奇计大败魏军,并射死庞涓。后来,田忌被邹忌排挤,流亡到楚国,孙膑大概也随他而去,所以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3.41 万字 | 2019-04-07 20:40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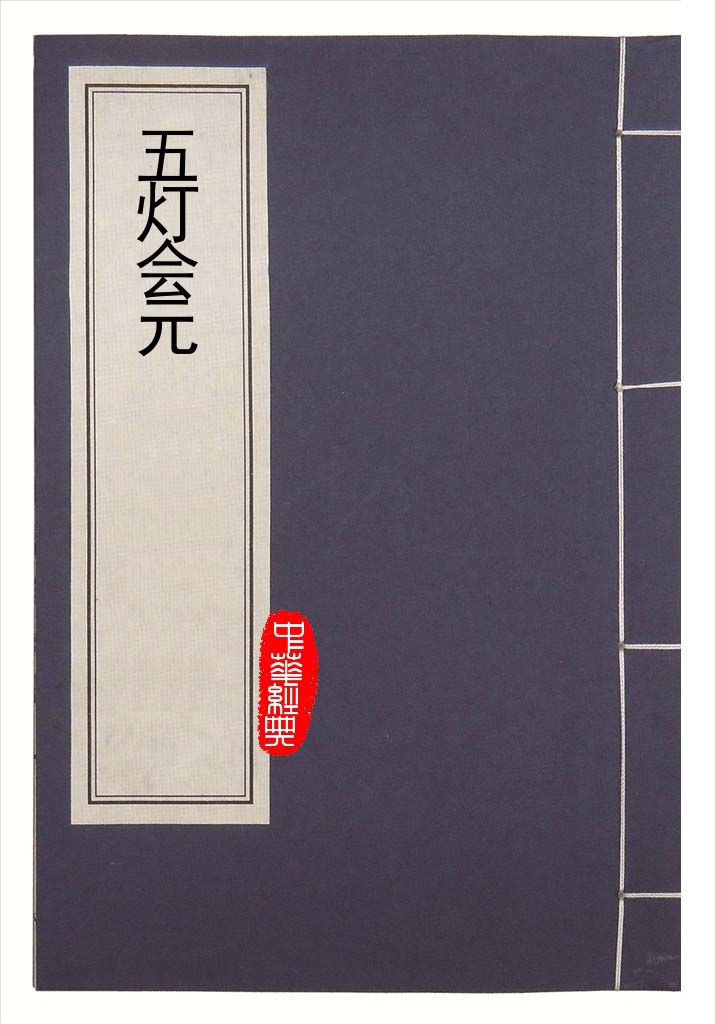
《五灯会元》是宋朝释普济将《景德传灯录》等五种重要灯录汇集删简而成的,共二十卷。《五灯会元》流传于世,不仅为内学者提供了禅史研究的丰富资料,而且也扩大了外学者的视野。“禅宗语要,具在五灯!”
94.24 万字 | 2019-04-07 14:29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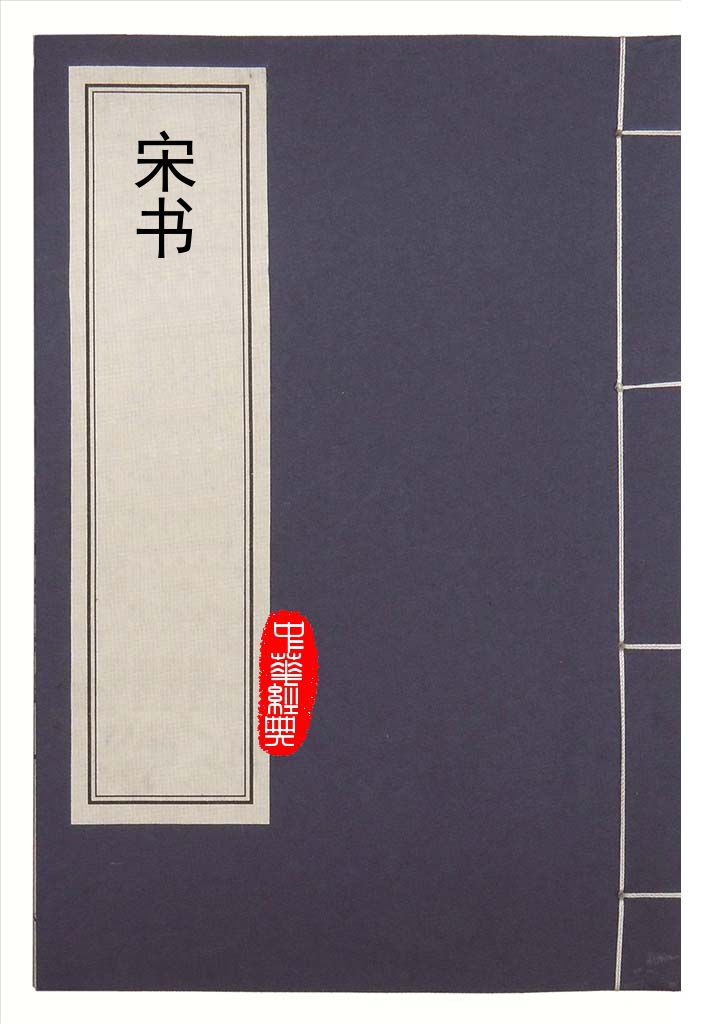
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梁沈约撰。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四○三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刘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今南。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又为萧齐所灭。 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鄒衍为鄒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二年)以后了。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於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沈约(公元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併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佔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誇,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梁武帝萧衍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杨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 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佔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於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传中只是连篇累牍收载他给友人的信,却说他「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於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 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礙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於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佔,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採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於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於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 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料学水平的著作。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输廓。 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叶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叶,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慤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採南史等书补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於「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於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阙」字。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106.12 万字 | 2019-04-05 16:14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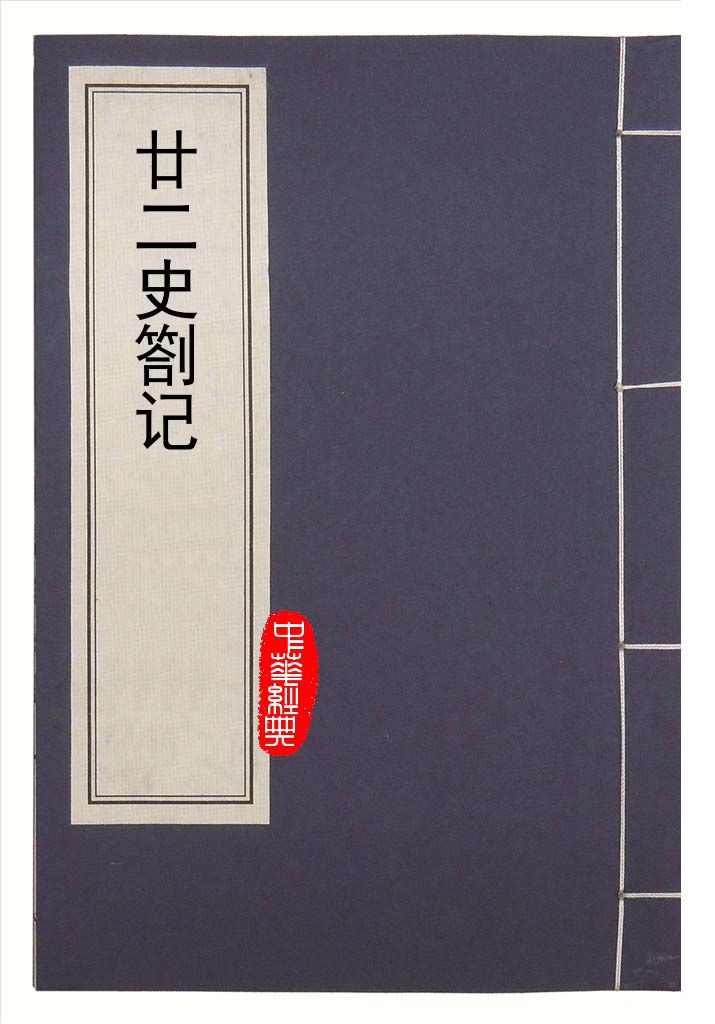
廿二史劄記 作者:清 趙翼撰作者:清 趙翼撰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為清代史學考據重要著作(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歷史考據三大名著)。其以筆記條列方式,考據包括史記至明史等二十四史,(其時舊唐書及舊五代史尚未列入正史,故稱二十二史)計三十六卷,補遺一卷。內容主要就史書的編撰編撰過程、時間,史料來源、真偽)、體例(異同優劣)加以考據,兼論政事、制度、人物之優劣臧否。
53.51 万字 | 2019-04-06 22:40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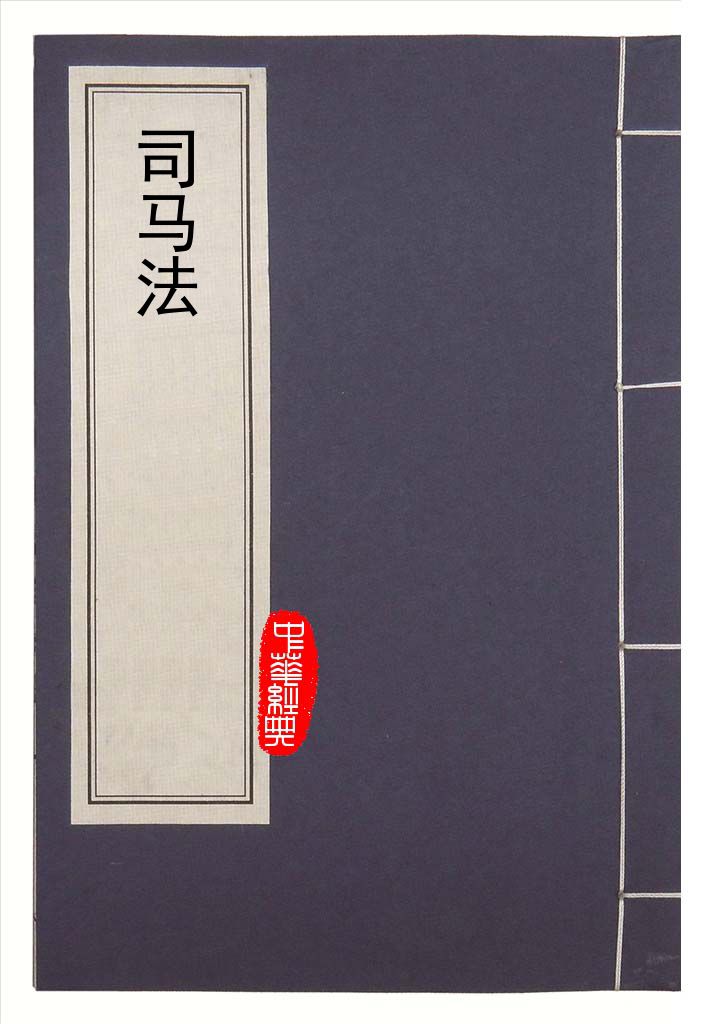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姜子牙所写,但到了战国时已经散失。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一百五十五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三卷五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三卷五篇的原型。 此书受到歷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本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 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歷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歷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 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一百五十五篇仅存五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週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感谢隽心指正“着名”错误。
0.51 万字 | 2019-04-07 21:16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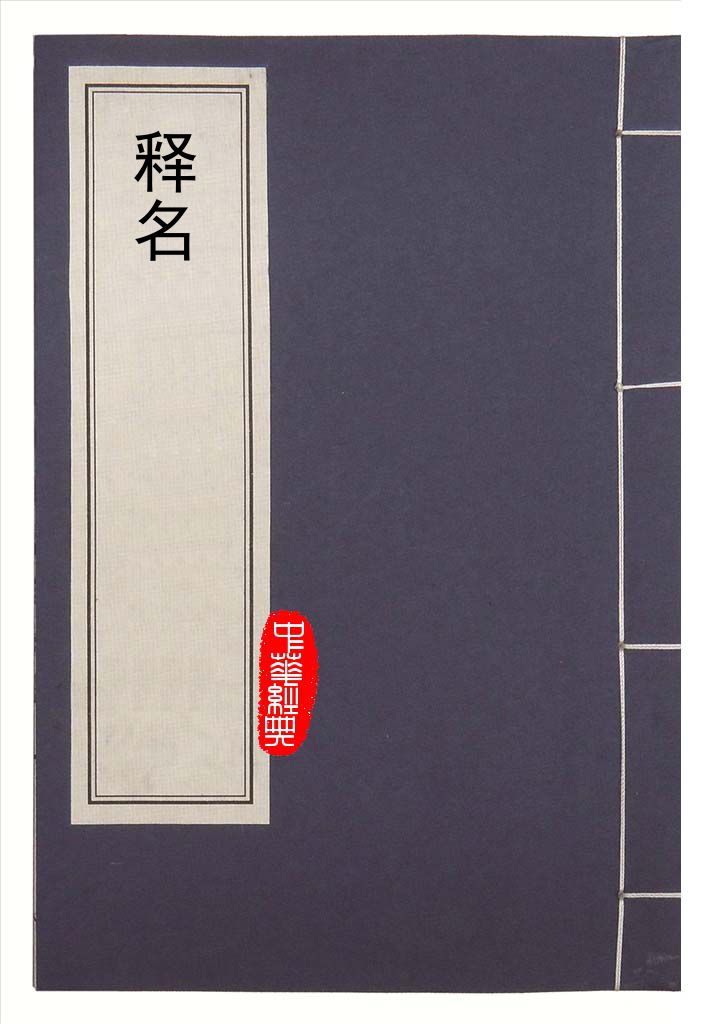
“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 大千世界,万物纷呈,其名各异。百姓大众呼物品而欲究其得名之由。适应这种心理需要,我国东汉末年出现了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这就是《释名》。 《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北海(今山东省寿光、高密一带)人,生活年代当在桓帝、灵帝之世,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献帝建安中曾避乱至交州,《后汉书》无传,事迹不详。 《释名》共8卷。卷首自序云:自古以来,器物事类“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说明刘熙撰此书的目的是使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原由或含义。其27篇依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虽不够完备,但已可窥见当时名物典礼之大概。 刘熙解释名源,采用的是声训的方式。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采用。汉代《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著作中,声训用得也很多。但全书的名物语词都用声训来解释,则《释名》为第一书,是刘熙的独创。 《释名》中的声训,从训释词和被训释词的关系来看,大致有几种情况,即:或同音,如“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 “勇,踊也,遇敌踊跃欲击之也。”贪与探、勇与踊同音;或音近,如“罵,迫也,以恶言被迫人也。”(罵,鱼部明纽上声字;迫,铎部帮纽入声字);或双声,如“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河、下皆匣纽);或叠韵,如“月,阙也,满则阙也。”(月、阙皆在月部)《释名》在用一个字做声训之后,还接着说明用该字释义的理由。如“探取入他分”,说明了以“探”释“贪”的原由;“满则阙”,说明以“阙”释“月”的原由。这样也就从音义的结合上说明了一个名称的来由。 《释名》用声训解释名物典礼,有些讲得较贴切,有些则为穿凿杜撰之说。如“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释用器》)“发,拔也,拔擢而出也。”(《释形体》)“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释天》)这样的解释显得十分牵强。其实世上事物得名的途径很多,情况非常复杂。而通过声音线索由一物名衍生出另一物名,只是起名的一种途径而已。而且有的名称由约定俗成而来,仅仅是记录事物的一种代号,音与义之间并无联系。所以对事物之名如果全通过声训来解释,势必出现悖误。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释名》“中间颇伤穿凿”。不过,远在1700多年以前,刘熙能写出这么一部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实在可贵。 《释名》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汉代4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为: 1。《释名》以声训解释名物,为因声求义开辟了道路,促使了古代韵书的产生。《释名》又集汉代音训之大成,为考见汉末语音,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特别可贵的是,《释名》中记录了当时一些语词的方言读法,如《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清、徐以舌头言之。”“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清、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 这些记录说明了汉代一些方言语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扬雄《方言》所没有的,因而十分宝贵。 2。《释名》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与《尔雅》、《说文》以及古代经典或传注相参证。如《说文。禾部》:“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释名。释州国》: “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润也。”此说正是秦“地宜禾”之证。尤其是《释名》中有许多与《尔雅》、《说文》及经传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训释,是很有价值的训诂材料。如《诗。邶风。泉水》:“我思肥泉。”毛传:“所出同,所归异曰肥泉。” 出自同一源头而流向异处的泉水为何称为“肥泉”?《释名。释水》曰:“本同出时所浸润少,所归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 刘熙说明了原委,比毛传更进了一步。又如《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释名。释长幼》曰: “七十曰耄,头发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铁也,皮肤黑色如铁也。九十曰鲐背,背有鲐文也。”这一解释有异于《曲礼》,内容也较丰富。又如《说文》:“瓦,土器也,已烧之总名。”瓦本指烧制的陶器。《释名。释宫室》:“瓦,踝也,踝,坚确貌也。”这里所说的瓦是指盖房顶的瓦(古瓦有当,向外。 瓦与当连,犹如人足与踝相连,故以“踝”释“瓦”)。这说明至少在汉末“瓦”的词义已发生了转移。这类材料对我们探讨词义学和汉语史都很有价值。 3。《释名》还保留了汉代的一些古语。如《释天》:“露,虑也,覆虑物也。”“覆虑”是古语,亦谓之“覆露”,在《汉书。晁错传》、《严助传》、《淮南子。时则篇》中都曾出现,是“荫庇”、“霑润”之义。《释天》:“虹,又曰美人。”这是古代俗称。传说古时有一对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为美人虹。《释丧制》:“汉以来谓死为物故。”“狱死曰考竟。”这些古语,传达了上古时代语言的信息,可以作为考察古今语言发展轨迹的凭据。 4。《释名》所训释的对象不侧重于文献语言,而重于日常名物事类,因此它涉及社会生活面广,从天文、地理到人事、习俗都有所反映,加上《释名》成书去古未远,所以可以因所释名物推求古代制度。如《释书契》:“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说明汉代册封侯王时立有整敕其不得犯法的文书。又如《释典艺》:“碑,被也。 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 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碑的功用的演变由此可见。原来,古时丧葬,在墓坑两端各树一石碑,碑间架辘轳,以绋绕辘轳上,挽棺缓缓下放。后来碑用来追述先人功业。《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由此我们可了解古代朝会时大臣所执手板的用途。《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 汉代的裲裆,相当于后代的背心。“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即披肩。前人认为始于晋,由此可见汉末就有了。 《释首饰》:“髲,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原来假发早在汉代就作为头饰了。“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也。” 珰的产生及其流传情况由此可见。《释用器》:“枷,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挝穗而出其谷也。”可见今天一些地区脱粒用的农具连枷的历史相当悠久。阅读这些记载,可以获得百科知识,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缘始和汉代生产生活情况。 从上所述可见《释名》对研究训诂学、语言学、社会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清人毕沅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释名疏证。序》)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释名》产生后长期无人整理,到明代,郎奎金将它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 因其他四书皆以“雅”名,于是改《释名》为《逸雅》。从此《释名》又别称《逸雅》。《释名》的明刻本缺误较多,清人对它进行补证疏解,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后者为清人研究整理《释名》的集大成之作。
0.26 万字 | 2019-04-05 15:10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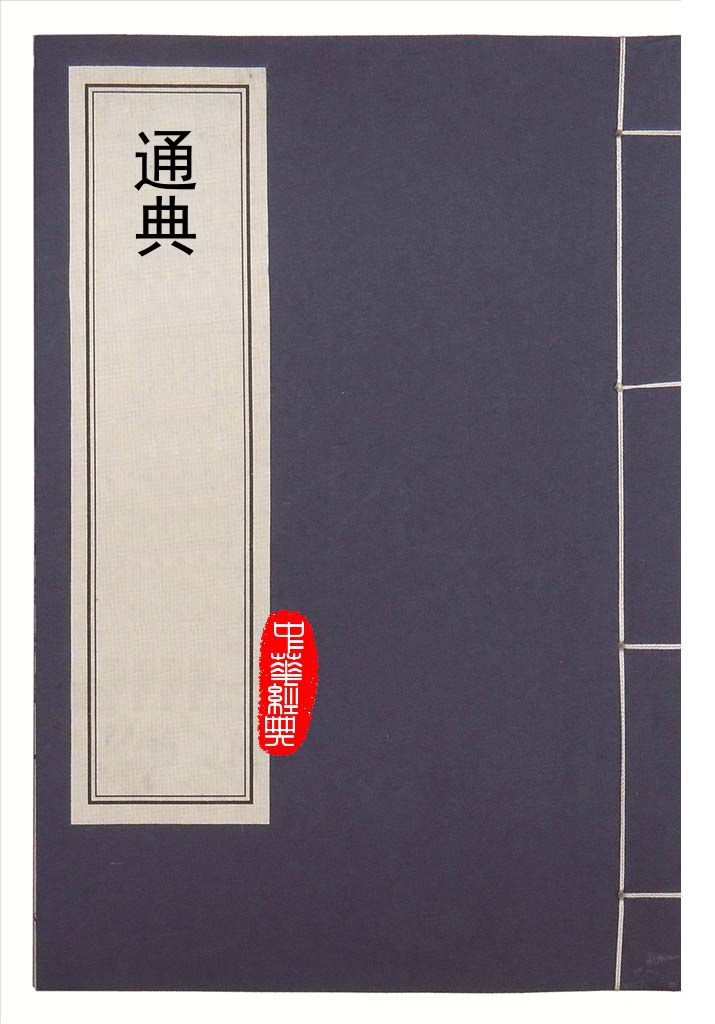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享年七十八岁。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三十五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69.40 万字 | 2019-04-07 13:42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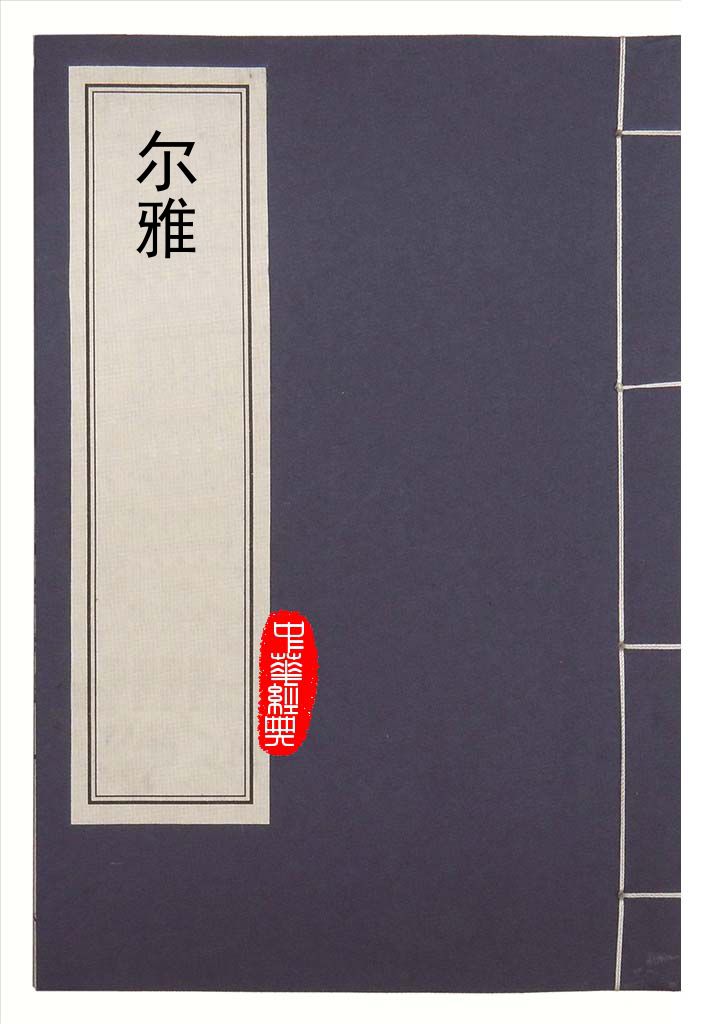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67年)生;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卒。博物学。 郭璞博学多才,一生不仅写了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而且做了大量的注解古籍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所注解的古籍有《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楚辞》、《三苍》和《方言》等等。这些古籍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动植物知识。郭璞对这些古代典籍,尤其是《尔雅》的注解,对中国古代动植物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语词的著作。它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全书19篇,其中最后7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中。《尔雅》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据史书记载,东汉初,窦攸由于“能据《尔雅》辨豹鼠”,所以汉光武帝奖赏给他百匹帛,并要群臣子弟,跟从窦攸学习《尔雅》。郭璞更是把《尔雅》视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了解大自然的入门书。他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但是,《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加上长期辗转流传,文字难免脱落有误,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不少内容,不易被人看懂。因此,在郭璞之前已经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郭璞从小就对《尔雅》感兴趣。他认为旧注“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于是“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并参考樊光、孙炎等旧注,对《尔雅》作了新的注解。 郭璞研究和注解《尔雅》历时18年之久,对《尔雅》所载之动物和植物进行了许多研究。首先他以晋代通行,或当时某地方言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鸠,◆◆”,郭璞注曰:“今之布谷也。江东呼为获谷。”《尔雅·释木》:“◆,山◆。”郭璞注曰:“今之山楸也。”这类注解,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只是以名词解释名词。而实际上却不那么容易,它需要丰富的训诂知识和实际经验。另外,这类注解虽然只是名词解释名词,但实际上它是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和当时为一般群众所认识的动植物联系起来,从而使古老的名称具有以当代一定实物为基础的含义。例如,《尔雅·释虫》中有“国貉,虫◆”的记载。如果不看注解,人们很难理解“国貉虫◆”的含义。郭璞注云:“◆”,“今呼蛹虫”,并引证《广雅》云:“土蛹,◆虫也。”所谓蛹虫,就是指寄生于蚕蛹体内的蚕蛆蝇幼虫。郭璞的注解,将古老的“国貉”、“虫◆”等动物名称和当时养蚕生产上广泛存在的蚕蛆蝇幼虫联系起来。郭璞《注》中,经常出现“今言”、“俗言”、“今江东”等提法,仅《释草》中就出现50多次,这说明郭璞对《尔雅》的研究,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由于能由今通古,所以他的注解,无形中复活了许多古老动植物名称。 郭璞丰富和发展了《尔雅》对各种动植物的具体描述。郭璞是山西人,因战乱逃至江南,并经常往来于长江中下游,所以他对许多地方的动植物,都有所了解。他注解《尔雅》,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各种动物和植物的通名和别名,而且根据自己从实际中获得的知识,对多种动物或植物的形态、生态特征,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例如鲟鱼,《尔雅·释鱼》仅记其名为“◆”,无它释。但郭璞则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大鱼,似◆而短鼻,口在颌下,体有邪形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这里郭璞很逼真地描述了鲟鱼的形态特征。《尔雅·释虫》“◆,啮桑”,郭注云:“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将桑树害虫桑天牛的形态和习性作了描述。又如对《尔雅·释木》中提到的“白◆”(即扁核木),郭璞《注》云:“◆,小木,丛生,有刺。实如耳◆,紫赤,可啖。”对“活◆”(即通脱木)郭璞《注》说:此“草生江南,高丈许,大叶,茎中有瓤,正白”。这些描述,虽然还很粗糙,但它不仅大大发展了《尔雅》的分类描述,而且对后来的动植物分类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郭璞开创了动植物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尔雅注·序》记载,郭璞不仅为《尔雅》作文字注解,还为《尔雅》注音、作图。《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尔雅图》十卷,郭璞撰”。可见大概在梁代,人们还看到有郭璞所作的《尔雅图》。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尔雅音图》,乃是清代嘉庆六年(180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所为之《尔雅图》。当然,即使如此,经过长期辗转重摹和翻刻,现在的《尔雅音图》也不可能还是原来《尔雅图》的原貌。但是现在看到的《尔雅音图》的情况表明,凡是郭璞有注解的动植物都有图。相反,凡是虽为《尔雅》所著录,但因郭璞暂时不识,而未作注解的动植物则无图。这说明图完全是配合文字注解而作的。因此《尔雅注》所解释的动植物,不仅有简要的文字描述,而且配有实物图像,实为动植物志的雏形。这是我国动植物分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生物学史上,郭璞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他的研究和注解,使《尔雅》所包含的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使得原来难读的《尔雅》,也成为能够读懂和能够利用的书。《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著名的《证类本草》一书,大量吸收了郭璞注解《尔雅》的成果。而《证类本草》又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蓝本。从郭璞以后,图文并用描述动植物的方法,也在本草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唐代以后,所有大型本草著作都配有图。 郭璞对《尔雅》中所著录的动物和植物,凡是他自己暂时还没有弄清楚的或没有听说过的,他都不强作注解,而是注明“未详”或“未闻”等字样。这说明他作学问的态度,是谦虚谨慎和实事求是的。 郭璞为注解古籍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尔雅》注后来被列入《十三经注疏》。他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公元316年,他因献《南郊赋》而被任为著作佐郎,后迁尚书郎,再后为割据荆州的王敦辟为记室参军。他最后因多次谏阻王敦谋反而遭杀害。
2.94 万字 | 2019-04-05 13:36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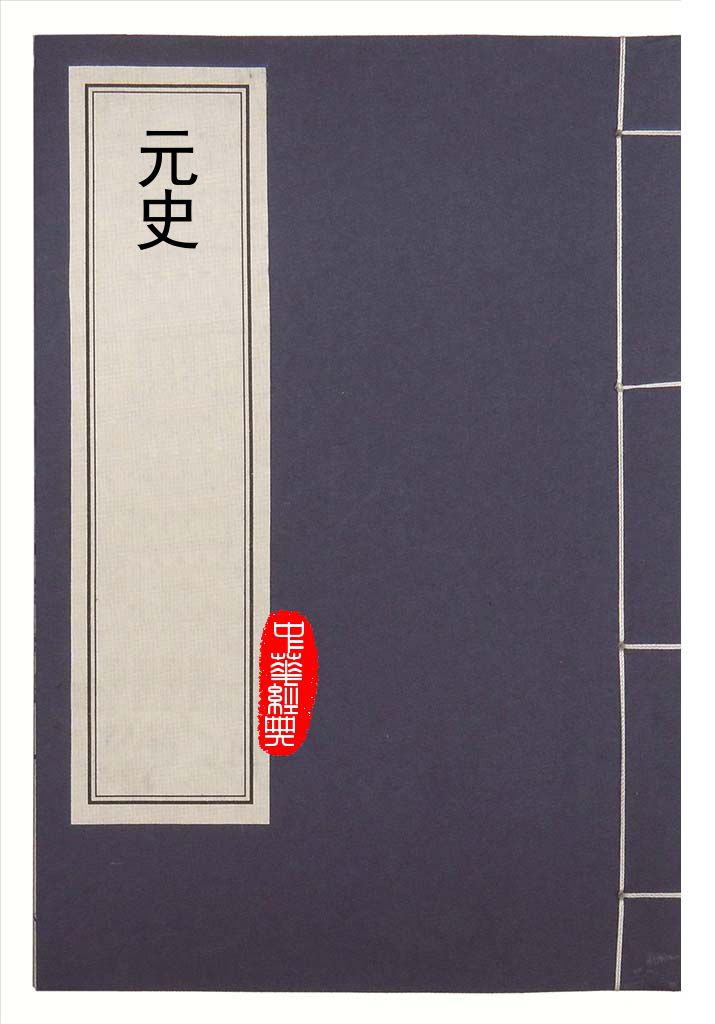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载我国历史上元代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即元朝滅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壎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局编写。仅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讓欧阳佑等十二人四出蒐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於洪武三年(一三七○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由朱右等十五人参加编写,用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本纪、志、表、列传共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二书,釐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刻印工作也进展得很快。据宋濂目录后记,洪武三年七月书成,十月便已「镂板讫功」。 元史之所以能迅速成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元史的编修,主要是照抄代各朝实录、经世大典、功臣列传等官修典籍,除了删节以外,没有下多少功夫。就元史编者的政治观点来说,同那些编修代典籍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信奉的都是儒家道学思想,所以在处理前代王朝遗存的历史资料时,也就无须从思想观点上和内容编排上作根本的改动。这样,元史编者们便无意中更多地保存了元代史料的原貌。 对於我们研究元朝的历史来说,元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本资料。四十七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全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历朝实録的摘抄,内容比较丰富,是按年月日编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大事记。史料价值和确切性都比较大。有些旧学者指责元史本纪「不合史例」,内容「杂芜」,这是一种偏见。五十八卷志、八卷表的史料,除顺帝朝部分之外,绝大部分採自元文宗时所修的经世大典,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许多内容只能在元史各志中看到,因而顯得珍贵。至於九十七卷列传,大部分取材於元朝官修的传记,而这些官修传记又是根据家传、神道碑、墓志等写成的。因此,在记载的确切程度上,要比纪、志差得多,但是其中含有许多生动具体的资料,这一点又是己、志所不及的。 由於元史仓促成书,且出於众手,在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例如:有一些列传重出;甚至误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领取岁赐的名单,统统当作同一皇帝的后妃处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将儿媳、曾孙媳、玄孙媳妇当成平列的妻妾。此外,译名不统一、年代史实的乖误等,也相当多。因此元史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试图重修元史的书出过好几种。但是,这些重修之作都无法取代元史这部比较原始的基本资料。 元史最早的版本是洪武三年刻本。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元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板,损坏的板页加以补刊,一般板心刻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此为南监本。南监本后来的遞修补刊一直延续到清初。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至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此为北监本。到清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武英殿又仿北监李重刻元史,称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对辽、金、元二一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这就是道光本。道光本对史的任意改动很大,但对史文也作了不少有根据的校订。后来又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其中比较好的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於洪武本的面貌。我们这次点校,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对百衲本在影印过程中的描修错误,用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北京图书馆藏另一部南监本作了核对订正,一律迳改。迳改的描修错误,共有近八十处。在版本校勘方面,用了北监本、殿本和道光本。还参考了胡粹中元史续编(简称续编)、邵远平元史类编(简称类编)、毕沅续资治通鑑(简称续通鑑)、魏源元史新编(简称新编)、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简称蒙史)、柯劭忞新元史,以及钱大明廿二史考异(简称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證(简称本證)等书。此外,并利用了批常见的原始资料,校正有关的史交,其书名和篇名,见於各卷的※校勘记。 本次校勘,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改动底本的地方,用方圆括号表圆括号内小字表示删,方括号内的字表示补),并附简要的校勘记。书中的明显刻误,以及板刻破体字,都予迳改。经过推算在纪日干支下用方括号补入的朔字,校勘记里不再说明。对书中的古体、异体、俗体字,侭量作了统一。原书卷首的进史表、纂修元史凡例和宋濂旨录后记,移至书末作为附录。
197.89 万字 | 2019-04-05 15:37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