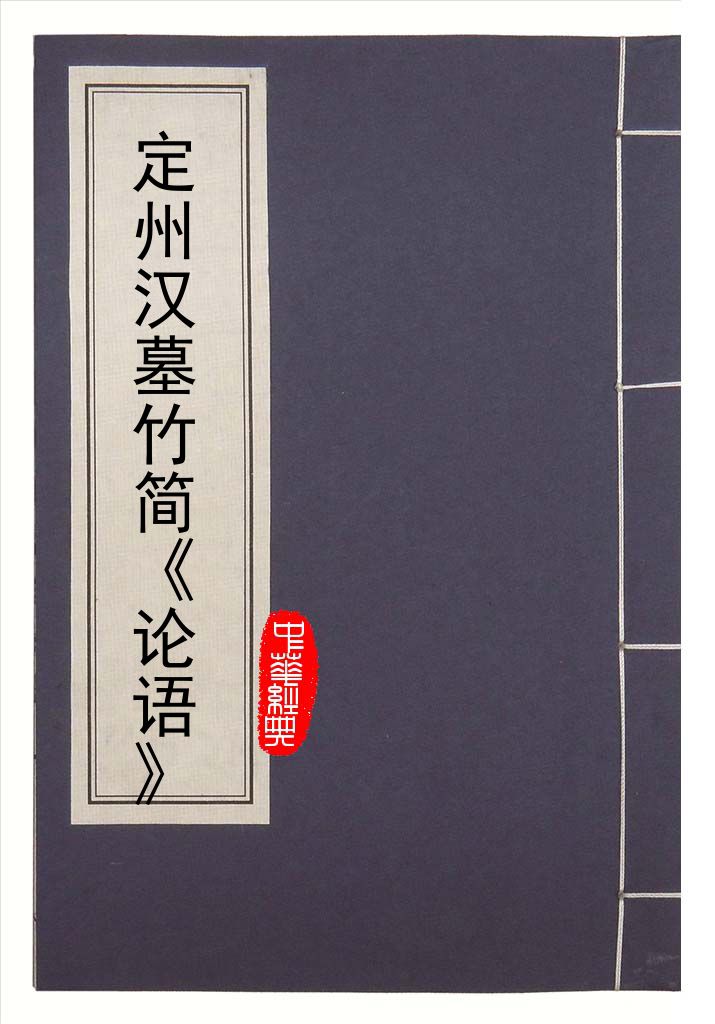
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是研究儒家学说和古代文字演变的新材料,值得重视。<br><br> 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将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简本《论语》和《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比较后,指出定州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br><br>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位于定县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大约在西汉末年该墓曾被盗掘过,但由于盗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盗墓人惊骇逃出,致使该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虽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同时也因盗扰火烧,使竹简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坏。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已多不清晰。此外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尚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估计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等。<br><br> 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当时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编号、写释文)。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竹简虽经精心照管,但在转移中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简又一次散乱,并遭到一定的损毁。地震后于1980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出面召集,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定县竹简的整理工作才又得以继续。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br><br>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br><br> 此外各章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少出入。简本《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当时世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因此简本《论语》的出土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材料。<br><br> 关于该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撰写了《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在1981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联合撰写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对该墓出土的竹简的形制、内容做了大致的介绍,同时还刊布了简文中《儒家者言》的释文。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合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一书。书中对出土简本《论语》的版本、文句也做简单的介绍,同时还对《论语》的全部释文做了简单的注释和校勘。
最近更新 章數簡| 2019-04-05 1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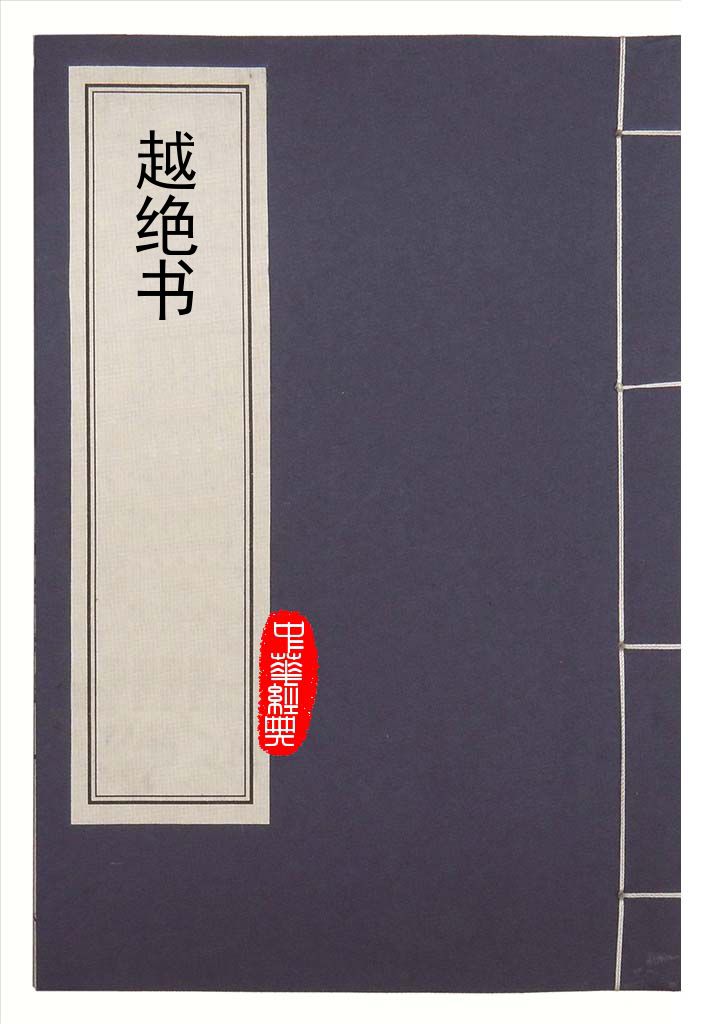
袁康,吴平辑(东汉) | 载记 | 连载中1817 点击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它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向为学者所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说明此书对于以上诸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br><br> 出于种种原因,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如关于成书年代,有春秋说、战国说、战国--西汉--东汉说、战国--东汉说、东汉初年说、东汉末年说、东汉初年--东汉末年说、西晋说;关于作者,有子贡撰说、子胥撰说、袁康撰说、袁康、吴平合撰说、袁康撰吴平修订说、袁康、吴平辑录说;关于卷数,有十五卷说、十六卷说;关于书名,有越绝书原称越绝说、越绝书原称越绝记说、越绝记非越绝书说;关于篇名,有吴太伯与兵法篇亡佚说、今本吴地传即古本吴太伯篇说、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即古本兵法篇说、今本陈成恒非古本陈恒篇说,等等。以上这些,一方面说明,关于越绝书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尚未统一,疑点犹待探讨;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正是由于越绝书的史料价值,在诸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使众多的研究者为之锲而不舍.
最近更新 越絕卷第十五| 2019-04-06 2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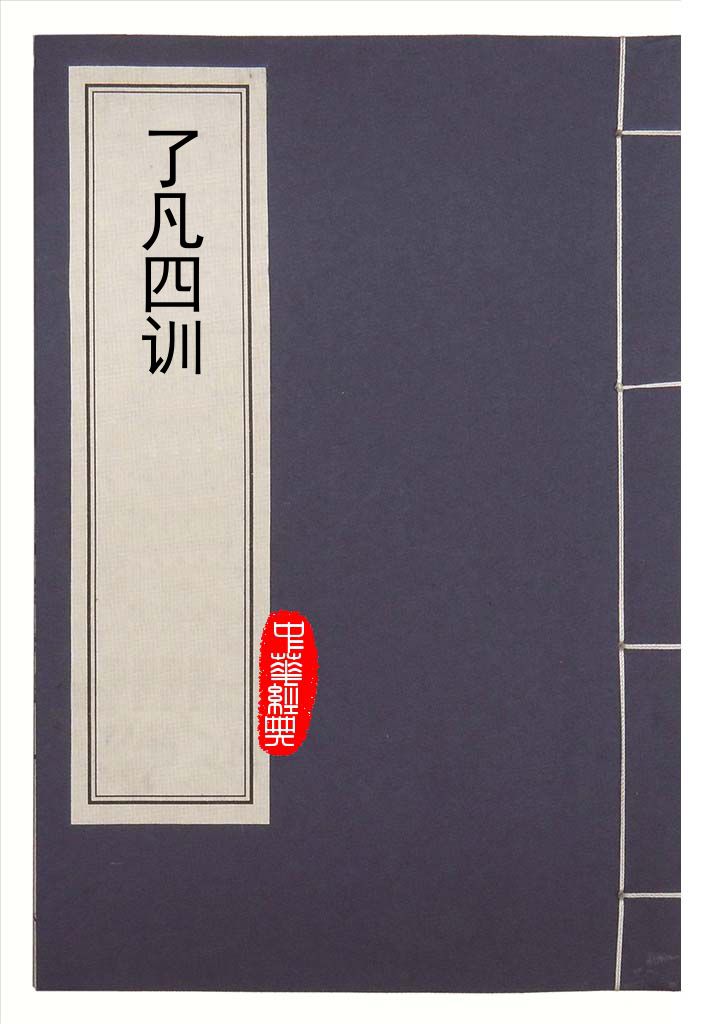
袁了凡先生,本名袁黄,字坤仪;江苏省吴江县人。年轻时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殳的人家;因此,在嘉善县得了公费做县里的公读生。他於明穆宗隆庆四年(西元一五七○年),在乡里中了举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考上进士,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过了七年升拔为兵部「职方司」的主管人,任中刚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鲜,朝鲜向中国求救兵。当时的「经略」(驻朝鲜军事长官)宋应昌奏准请了凡为「军前赞画」(参谋长)的职务,并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br><br>了凡先生家居生活俭朴,但每天诵经持咒,参禅打坐,修习止观。不管公私事务再忙,早晚定课从不间断。在这当中,了凡先生写下四篇短文,当时命名为「戒子文」,用来训诫他儿子,就是后来广行於世的「了凡四训」这本书。<br>==============================================================================<br>‘了凡四训’是一本初学佛必读的入门书,该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一生力行善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篇忠实报告,流传民间甚广。该文共分四篇,首篇谈‘立命之学’,使人了解命运之所由来,就如因果经上所说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要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始克有济。第二篇接著讲到‘改过之法’,这是因为一般人,都自认为自己是无过失之人,而不知改过行善。事实上严格来说,所谓‘过’,‘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同时行善之人,若诸恶不改,就有如漏了底的容器,无法积满,最多只能功过相抵,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改过’是‘立命’的下手功夫,是非常重要的。<br><br>人若知过能改,但不晓得行善的道理与方法,即使行善,有时往往也是徒劳而无益,甚至相反地,有时反而会造业。因此袁了凡先生在第三篇提出‘积善之方’,对于行善的方法,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与建议。最后鉴于一般初学行善的人难免会犯有‘众人独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志得意满与藐视一切的骄傲作风。所以了凡先生在末篇特别提出‘谦德之效’,叮咛‘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人若能谦虚为怀,则行善惟恐不足,如此方能使积善落实,以致达到改善命运的目的。<br><br>总之,‘了凡四训’确确实实是人生在世之至理名言,同时也是匡治目前社会风气败坏之最佳良法。凡欲改变命运,化凶为吉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求功名富贵,寿命增长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转病为健,转夭为寿,转穷为达,转罪为福,转凡为圣者,皆不可不读此书。深盼有福分之人一得此书,悉心持诵,坚立大愿,由解起行,如此不但自己的命运可改,家庭的命运可改,甚至国家社会的命运亦可随之改善,愿有志者共勉之!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信心勇气倍增,亟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最近更新 第四篇 谦德之效| 2019-11-01 1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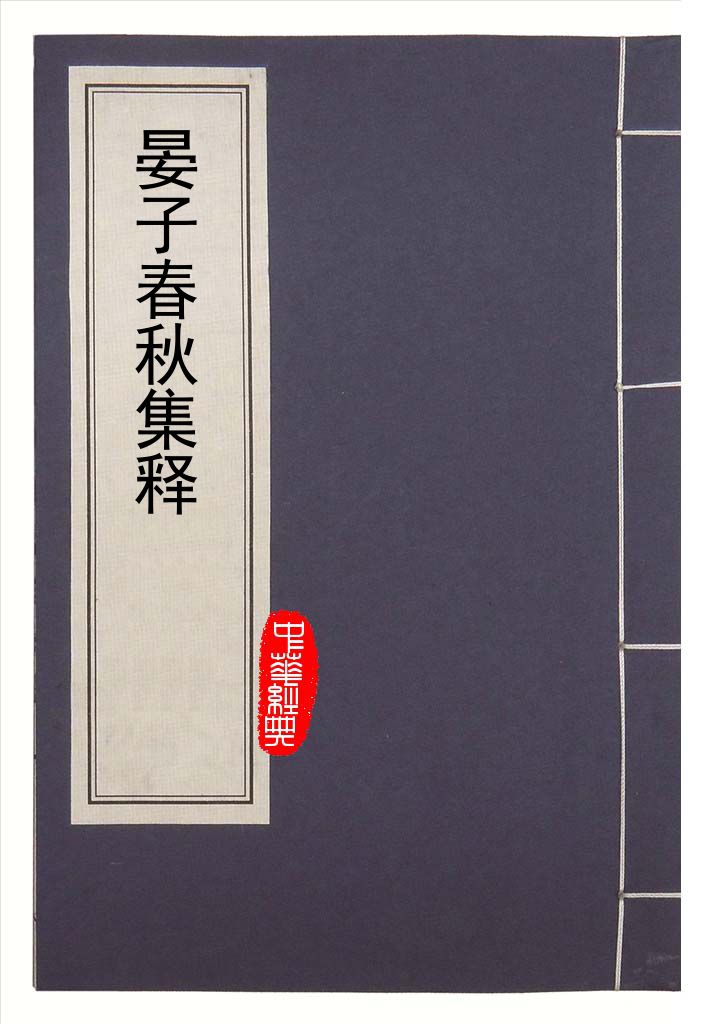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种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 书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 《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注释书籍有清末苏舆的《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代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参考价值较高。<br><br> 近代吴则虞编纂的《晏子春秋集释》对《晏子春秋》做了较为详尽的注释,是目前最好的注本,参考价值较高。<br><br> 吴则虞,当代哲学史家,历史学家.版本学家,安徽泾县人。1913年生,师从章太炎,在章太炎的指导下,精研古籍,攻读音韵.文字.训诂诸学,造诣很深。曾任南岳师范学院.重庆师女子范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央党校讲授中国哲学史,文字学,校勘学等课程。他喜爱收藏古今书籍,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藏书史,古籍校勘整理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工具书使用法》《版本校勘学通论》《版本通论》《晏子春秋集释》《晋书校勘记》《清真词校记》《稼轩词选注》《续藏书记事诗》等。
最近更新 晏 子 春 秋 重 言 重 意 篇 目 | 2019-04-06 2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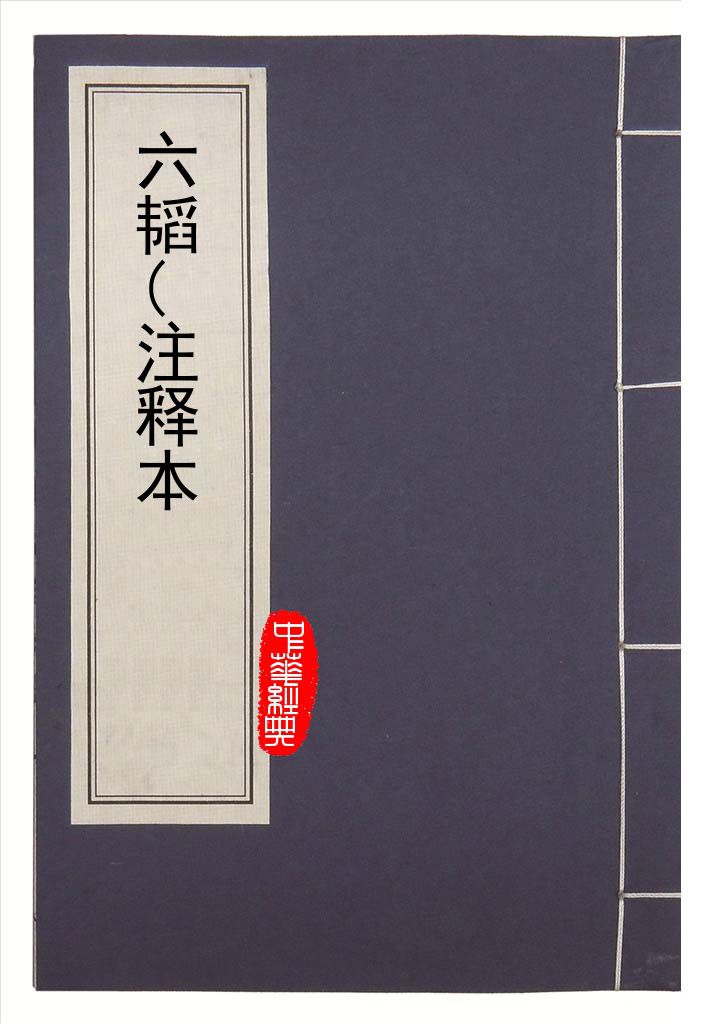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又称吕望,字子牙(一说字尚),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西周开国功臣、齐国始祖。历史上,对于《六韬》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书的真伪争议颇多。宋代以来,基本否定该书为吕望所作,认为是汉以后人伪托。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有《六韬》残简54枚,说明《六韬》在西汉前已流传于世,而非汉以后人伪托。当今学者大多认定《六韬》成书于战国时期。其理由是:《六韬》文辞浅近,与商周文字风格相去甚远,而与战国时期的《吴子》、《孙膑兵法》等相近。书中涉及骑兵作战的篇章很多,而骑兵诞生,是在战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书中提到的一系列铁兵器,都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另外,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也是战国时期的事。《六韬》成书于战国,当然就不是吕望所作,而是战国时人托其名撰成。<br><br> 《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兵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br><br> 现存《六韬》共6卷60篇,近2万字。版本约有20多种,重要版本有银雀山竹简本、唐代敦煌写本、唐代魏徵编《群书治要本》、《武经七书》本、《四库全书》本等。本电子版以《续古逸丛书》影宋《五经七书》为底本,对底本上明显的错、衍、脱、误之处,则参照银雀山竹简本、敦煌写本、《五经七书讲义》、《五经七书汇解》、《五经七书直解》等进行校改,底本错讹用()表示,校正的文字用[]表示。假借字和古体字一般随文用现代字替代,未替代的在注释中注明。
最近更新 卷六 犬韬| 2019-11-01 1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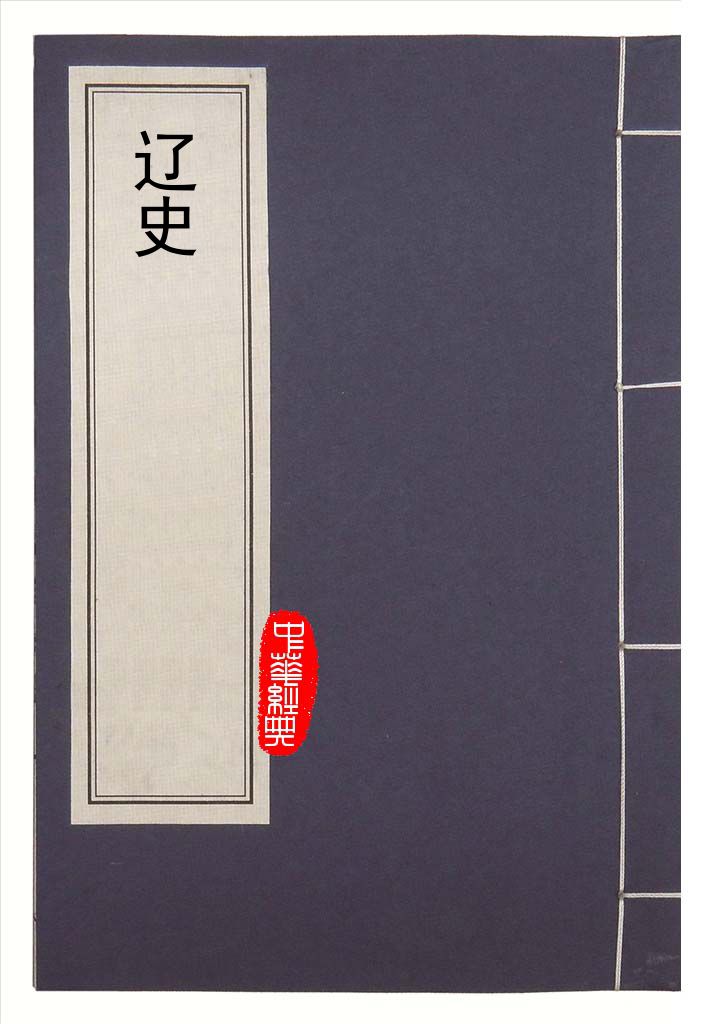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修,记载辽政权二百多年(公元九○七--一二五年)的历史。其中也兼敍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br> 契丹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各族之一,魏书、隋书等史都有传。唐末,封建军阀篡夺和瓜分农民起义的果实,在中原和南方各地分别建立自己的统治,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则在祖国的北方疆土上建立了辽朝。它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br> 辽朝和历代封建政权一样,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纂修实录。历次所修的实录,最后由耶律俨综合编订成书,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耶律俨,析津(今北京)人,本书有传。他的父亲耶律仲禧是在辽朝做官的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耶律俨本人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br> 从今本辽史可以考见,耶律俨实录包括纪、志、传等部分,为后来编写纪传体辽史打下了基础。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书为基本依据。第一次纂修在完颜亶(熙宗)时代,由耶律固、萧永祺先后执笔,皇统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宗成,未曾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於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決。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br> 元代中统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和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也由於「义例」未定,以至「六十馀年,岁月因循」。关於「义例」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於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个问题长期争议不決。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一二四三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決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各地人民相继起义,元政权处於风雨飘摇之中,财政又极困难,故三史都是仓促修成。其中辽史时间最短,只用了十一个月(至正三年四月到四年三月)。这次纂修即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鑑、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撰成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十六卷,就是现在这部辽史。<br>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認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複,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俨实録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br>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録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於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br> 辽史於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一三四五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勝於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於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过。另外,还用纪、志、表、传互校,并参考册府元龟、资治通鑑、续资治通鑑长编、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辽文汇等书校订了史文的脱误。对於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原书卷首有关修史的材料移作附录。
最近更新 附录 进辽史表| 2019-04-05 15: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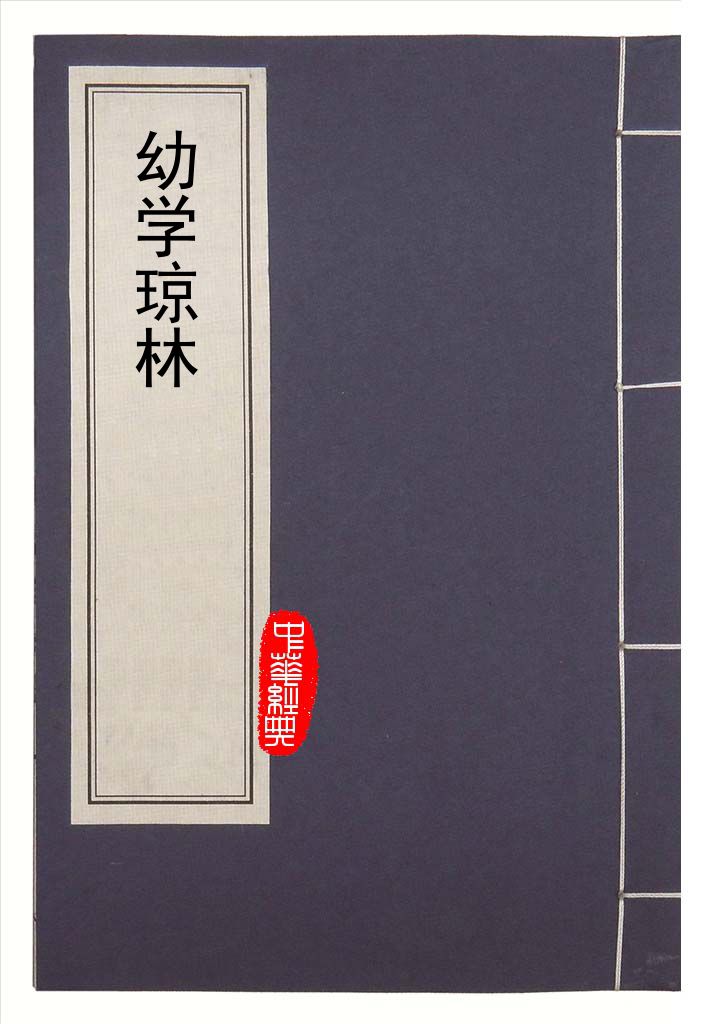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br><br>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着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後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包罗广泛,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做一些了解。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还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最近更新 卷四 花木| 2019-11-01 1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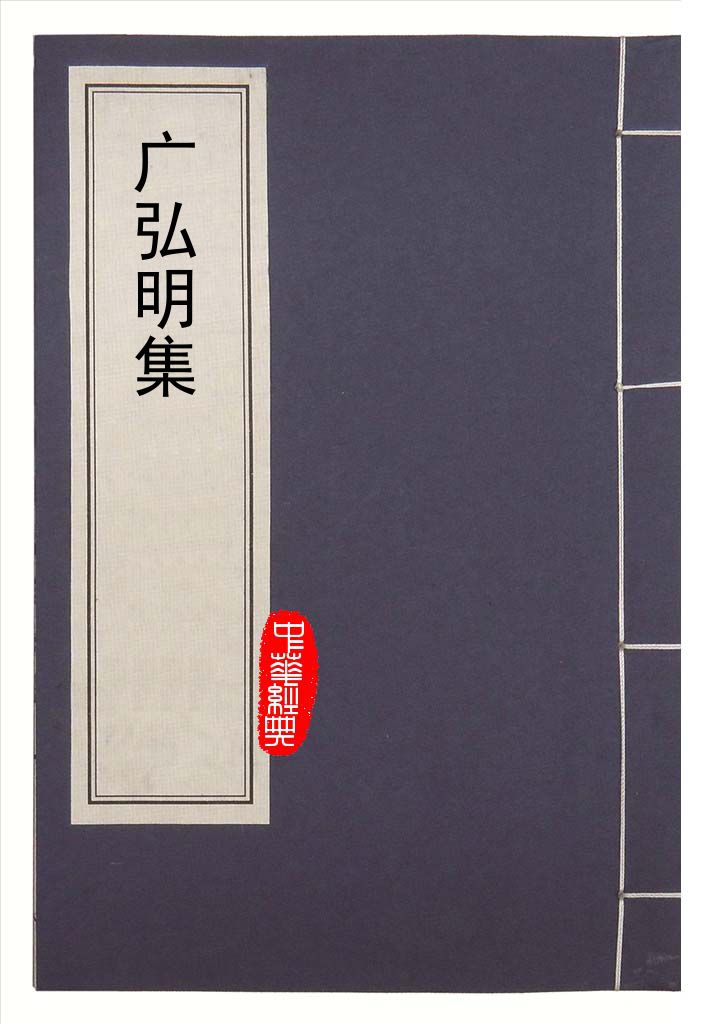
《广弘明集》,三十卷,唐京兆西明寺释道宣撰。这是继承、并扩大梁僧祐《弘明集》而作的书。在《旧唐书。经籍志》里,《广弘明集》虽与《弘明集》同列于丁部集录三类中的总集内,但它的体制和《弘明集》却稍有不同。《弘明集》分卷不分篇,《广弘明集》则除分卷而外,还按照所选文章的性质分为十篇:一、归正,二、辩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恻,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之前各冠以小序。不仅如此,《广弘明集》还用这十种范畴给僧祐《弘明集》所选的文章分类列目,而将它们收在除戒功、悔罪而外的八类中。又《弘明集》皆选辑古今人的文章,作者僧祐自撰的除末尾《弘明论》而外,只第十二卷开头有一篇小序,总计不过两篇。但《广弘明集》则除选辑古今人文章而外,作者道宣自撰的叙述与辩论的文章编入甚多。因此,《弘明集》仅是选辑、而《广弘明集》则叙述辩论与选辑并用。<br><br> 现在通行的《广弘明集》有两种版本:一为吴刻本(万历十四年丙戌吴惟明刻本,出于宋、元藏)三十卷;一为嘉兴方册藏本四十卷。<br><br> 本书撰述的主要宗旨,作者道宣在第十《统归篇序》的开头自己就说过,是为了“弘护法纲而开明有识”。这与《弘明集》的主要宗旨在于排斥异端而弘道明教的目的大致相同。<br><br> 本书所收重要资料,首先是佛道之争,主要的有三次:在北魏时代因太武帝信奉道教并由崔浩的进谗,北方佛教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北周武帝时代复因黑衣当王的谶记,并经道士张宾、卫元嵩的构陷,北方佛教又遭受了第二次毁灭性的打击,但同时道教亦受到破坏。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有沙门法琳与傅奕之争,这次佛教虽未受严重的打击,但后来韩愈辟佛,武宗毁法,直接间接都与傅奕的议论有关。其次是佛教思想史的问题,主要的有二:一在佛性问题,二为二谛问题。<br><br> 佛性是《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涅槃》源出《般若》,但《般若经》未明言佛性,所以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的鸠摩罗什虽宏《般若》而未畅说《涅槃》。门下道生始于佛性问题有大创见,即顿悟渐修说。道生以为佛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性,本性真实不虚,凡夫由无明而起乖异,是谓迷惑。以智慧力量除去迷妄,佛性自现,这是一个以不二的智慧冥契不分的真理而豁然贯通的顿悟过程。但觉悟非是自然生起,有赖于教与信修,即渐的功夫。道生的顿悟渐修说,大致如是。谢灵运作《辩宗论》并与法勗等诸家往返答辩,主顿悟信修说,而为道生张目。此外道生尚有阐提成佛说。<br><br> 道生当时所见《涅槃》经文为法显所得的六卷本,其中本无阐提成佛义。但道生独具只眼,竟说此经传度未尽。他以为佛性为众生本有之性,反本即得。所谓见性成佛者,不过此本性的自然显发而已。阐提既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既有佛性,当然也能成佛。道生之说虽受非难,六朝以后却大为盛行。<br><br> 其次二谛,是《般若》三论学的骨干。当《般若》学流行于晋代,宋、齐间《涅槃》与《成实》并盛,而成实师之说,易与《般若》相乱,它不但于人空外主张法空,并且还大谈二谛与中道。梁代成实师的代表如庄严僧旻、开善智藏、龙支道绰诸家都认为二谛可以相即而与《般若》三论说法抵触,因此,《般若》三论学者,不能不对成实师之说加以批判。从周颙作《三宗论》而攻难之后,双方争论遂络绎不绝。如梁武帝注《大品经》,昭明太子谈二谛并与二十二家往返议论,都对《般若》三论的弘扬有很大影响,而本集都保存了这些资料。<br><br> 此外,本书在北周佛道二教论争中所收的《二教论》、《笑道论》,又在初唐佛道论争中所收的《破邪论》、《决对废佛法僧事》、《辩正论。十喻九箴篇》等,也提供了中古宗教史上好多宝贵的资料。
最近更新 卷第三十| 2019-04-07 1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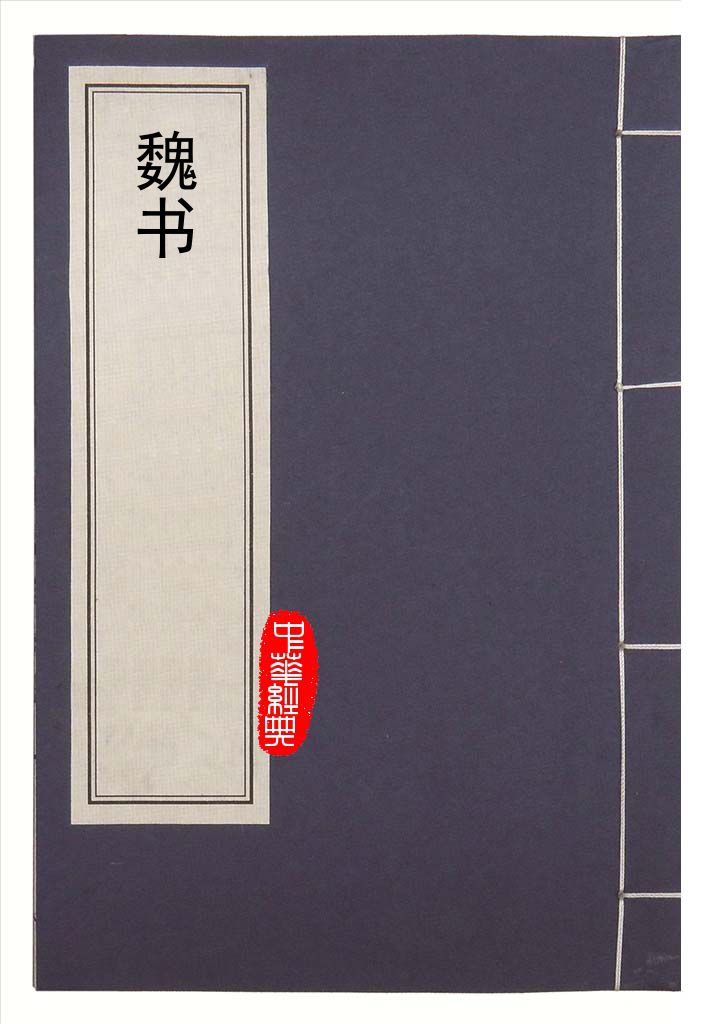
魏书一百三十卷(如不分子卷,则是一百十四卷),内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内容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兴亡史。<br><br>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馀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採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四八七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齐天保二年(五五一),高洋命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编写魏史,设置修史局,由太保、录尚书事高隆之监修,房延祐等六人先后参加修史。<br><br> 魏收(五○五--五七二)字伯起,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他是北齐著名文人,和温子昇、邢子才齐名。早在北魏末年他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掛名,魏收推薦的史官都是一向趨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br><br> 天保五年(五五四)秋,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br><br> 书成后,议论纷纭,被称为「秽史」。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他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还有受贿行为。由於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不平」的一百多人。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愔、高德正庇护魏收,逮捕了一些控诉的人下狱治罪,暂时压下这场风波,同时也命魏书「且不施行」。以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修改,始成定本,即传下来的这部魏书。<br><br>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br><br> 书中记载鲜卑拓跋部的早期活动,多少反映了拓跋部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材料。<br><br> 北魏承「十六国」之后,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书中列举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魏书自卷一百至一百三是国内少数族和外国的列传,大致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记录和口传写成。其中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载和传闻失实的地方,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各族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流的加强。<br><br>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br><br> 虽然如此,十志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四八五)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於货幣的记载,有助於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瞭解。灵徵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和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为后来姓氏书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併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别是反映了寺院所属奴隶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这不仅是有关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助於对当时全部封建剥削制度的瞭解。<br><br>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br><br>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一○六一)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一○六七--一○七○)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緻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於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遲不晚於政和中(八)。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最近更新 志第二十 释老十| 2019-04-05 1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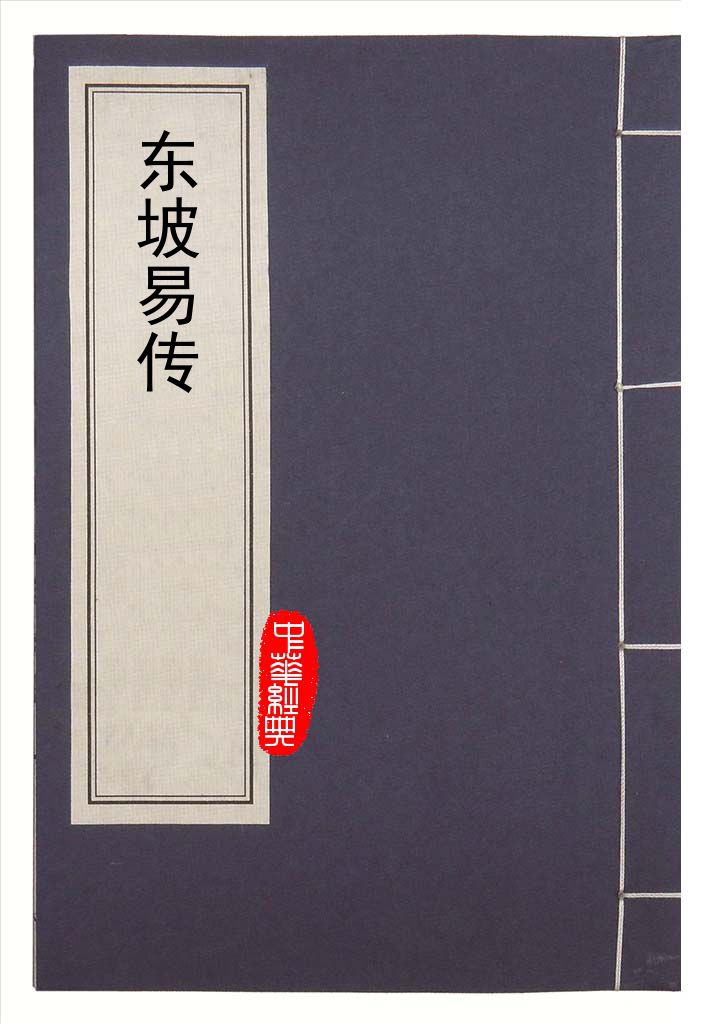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br><br>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后人不解《易》理,常常只识皮毛。然而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这本《易传》便被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本书作者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词赋无从谈起。”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最近更新 未 济 卦 (第六十四)| 2019-04-05 1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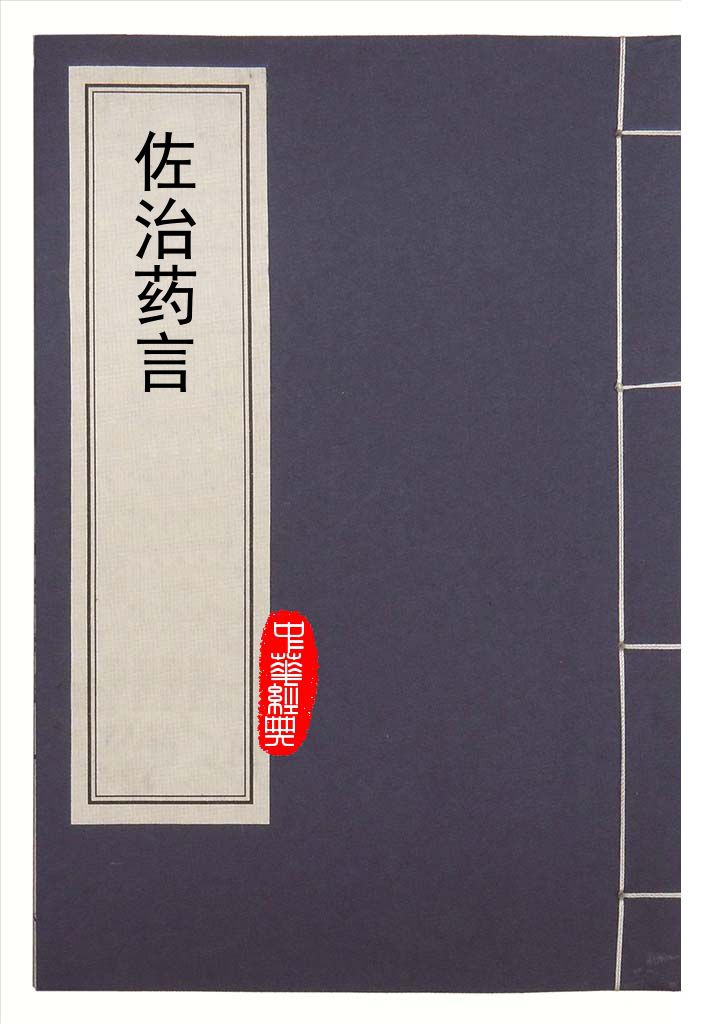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佐治药言| 2019-10-31 1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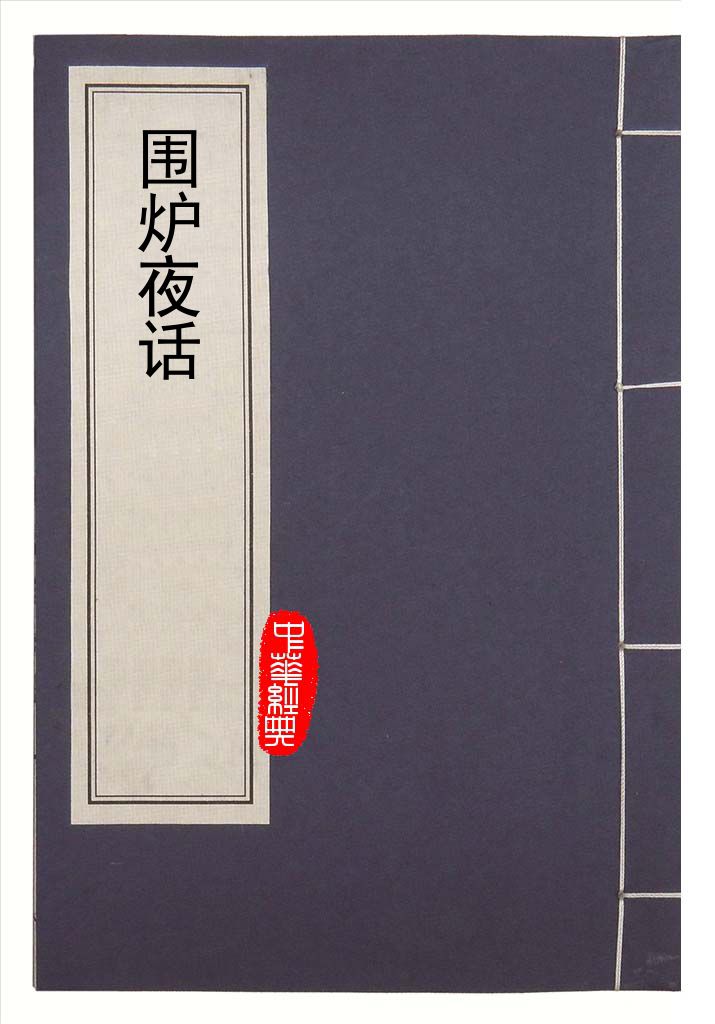
《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 夜是这样的美妙,更何况围坐在暖暖的炉边呢?静夜炉边独坐,品味清朝王永彬先生的《围炉夜话》,体味作者以平淡而优美的话语,讳讳叙出的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如炎夏饮一杯清凉的酸梅汤,令人神清气爽,茅塞顿开。<br><br>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速,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最近更新 围炉夜话| 2019-11-01 1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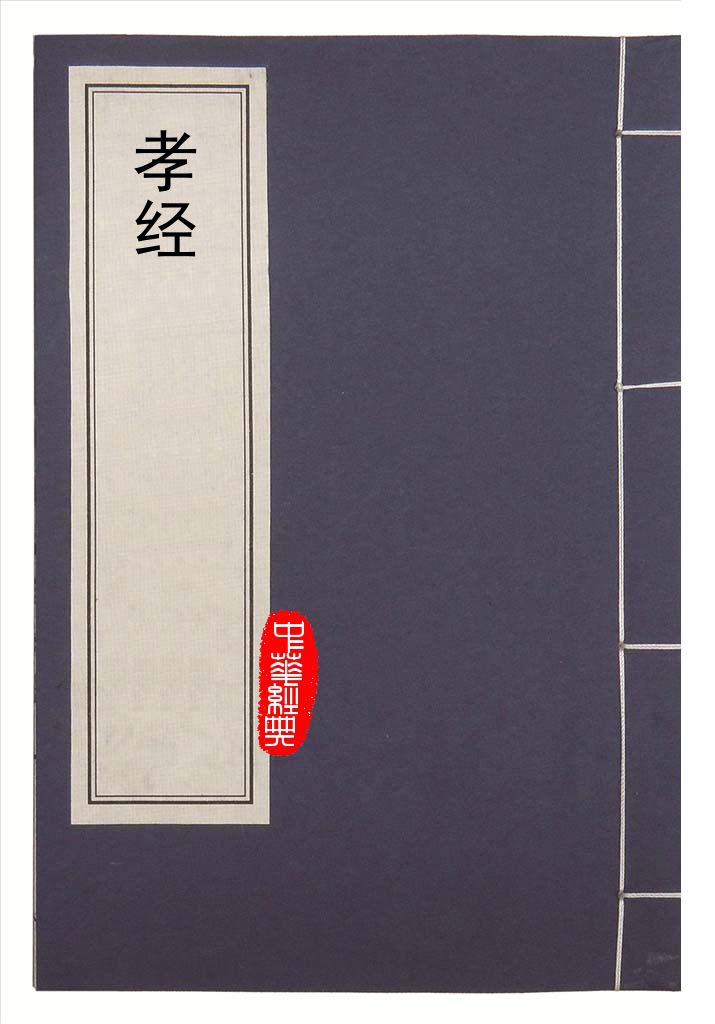
《孝經》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其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孔子說和曾子說等,學界一般認可為先秦儒者所作。<br> <br> 《孝經》以“孝”為中心,通過孔子與其門人曾參談話的形式,對孝的價值、意義、作用以及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闡述,是一部儒家孝倫理的系統化著作。 《孝經》認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孝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國家政治的根本。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共分十八章,全文不足兩千字,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短的一部。<br><br> 《孝經》在中國古代影響很大,歷代王朝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
最近更新 丧亲章第十八| 2019-09-25 1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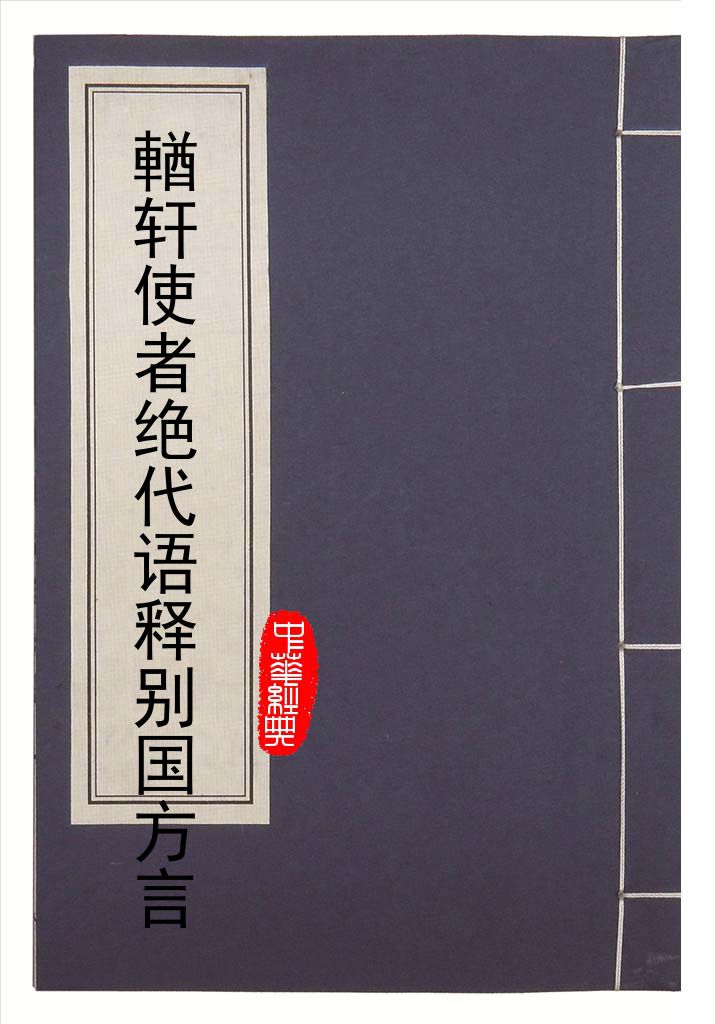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扬雄著,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而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br><br>中国土地广大,方言的地理差异悬殊,所以自古重视方言研究。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輶轩是古代使用的一种轻便车辆。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br><br>今传《方言》一书,据刘歆与扬雄书信往来及应劭所言,应为扬雄(前53—公元18年)所撰。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称书名皆始于应劭。<br><br>后世传本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br><br>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olo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最近更新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第十三| 2019-04-05 1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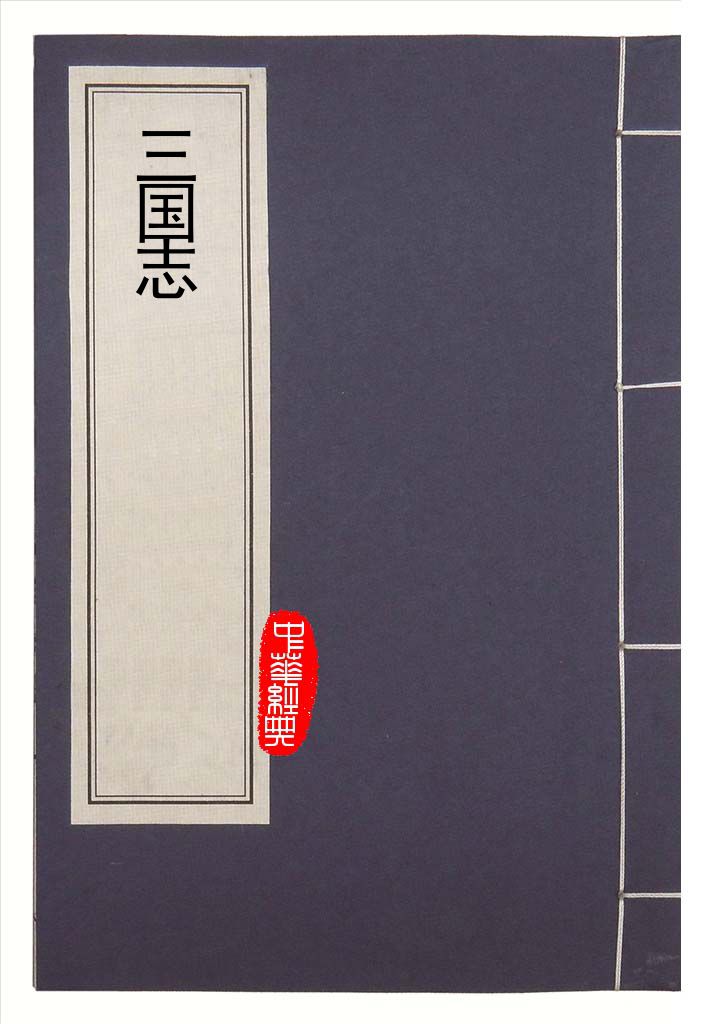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硃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讬始於魏文,而讬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br><br>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锺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类。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昬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最近更新 魏书 乌丸鲜卑东夷传| 2019-04-05 1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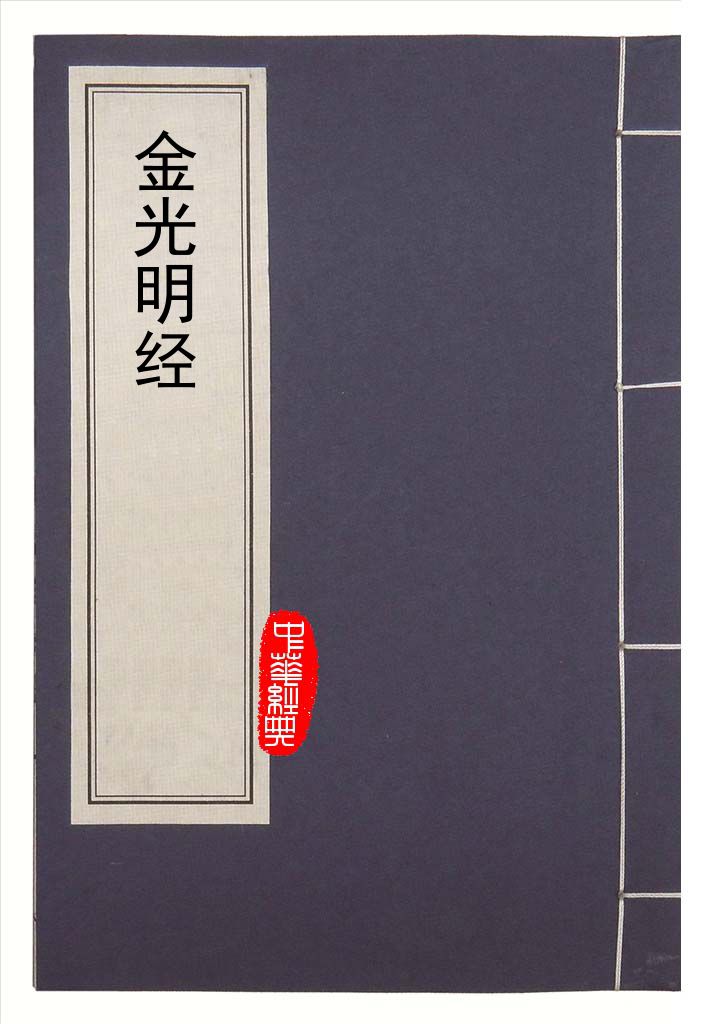
| 佛教十三经 | 连载中5110 点击
最近更新 卷四-嘱累品第十九| 2019-05-22 1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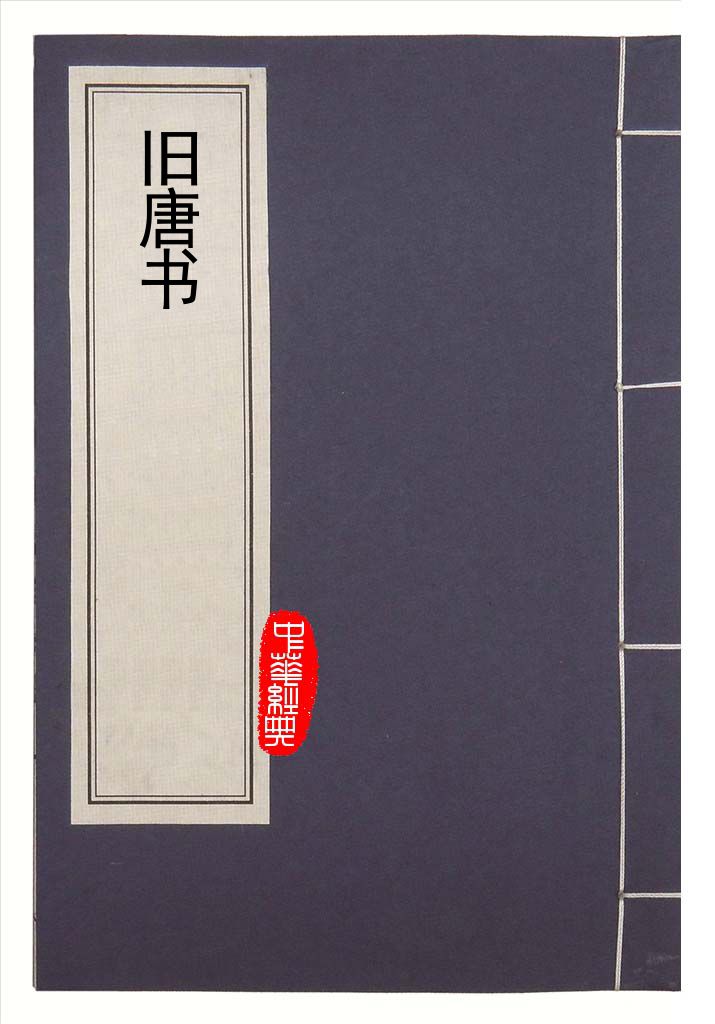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br><br>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確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纬等人。但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br><br>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br><br>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我们这次点校旧唐书,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简称懼盈齋本)为工作本,并参校了以下几种主要版本:<br><br>一、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br><br>二、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br><br>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br><br>四、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br><br>五、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br><br>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而根据唐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记说明。关于前人校勘成果,除参考清人罗士琳等人的旧唐书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外,还吸收了近人张森楷旧唐书校勘记、龚道耕旧唐书补校等几种稿本的某些成果。
最近更新 附录| 2019-04-05 1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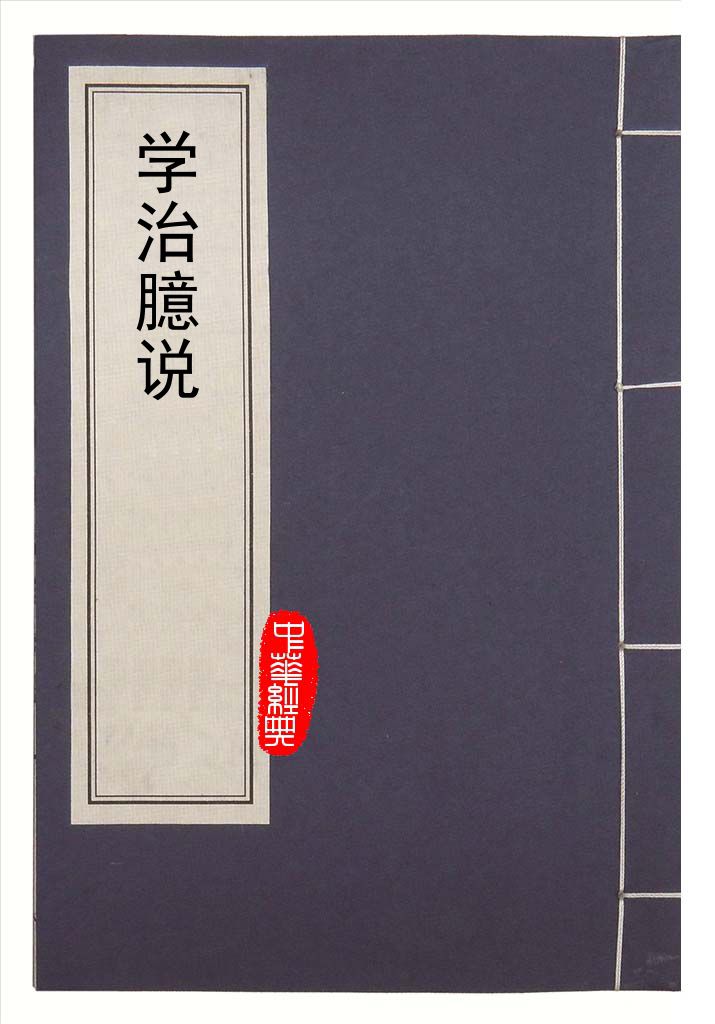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br><br>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br><br>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最近更新 译文| 2019-10-31 1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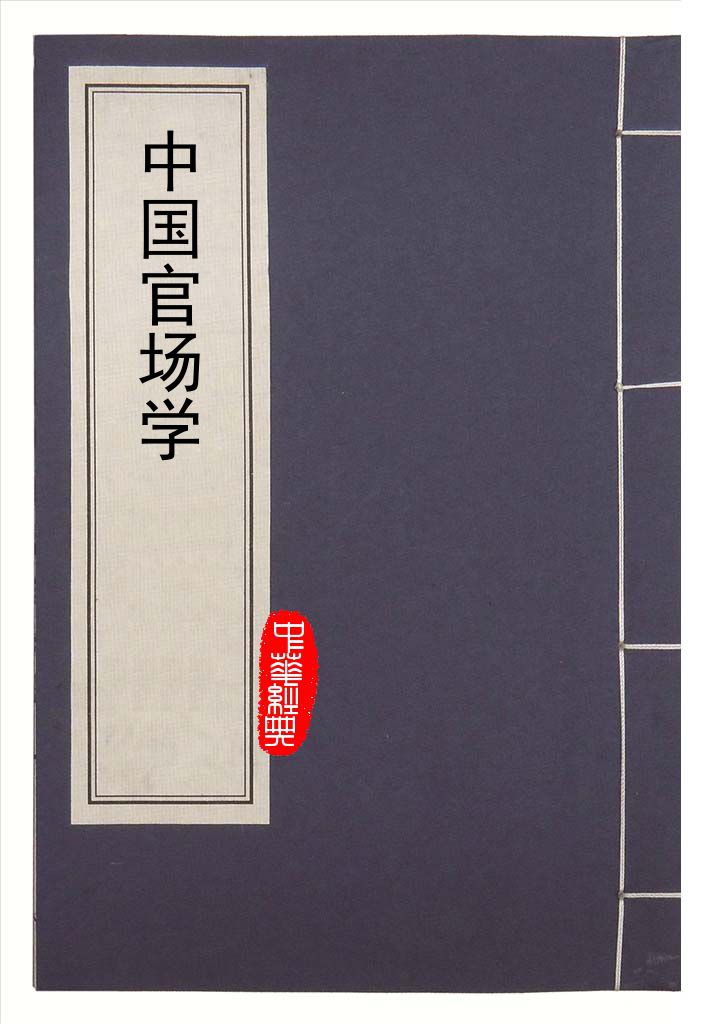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br><br>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最近更新 幕学举要 万维鶾| 2019-04-07 1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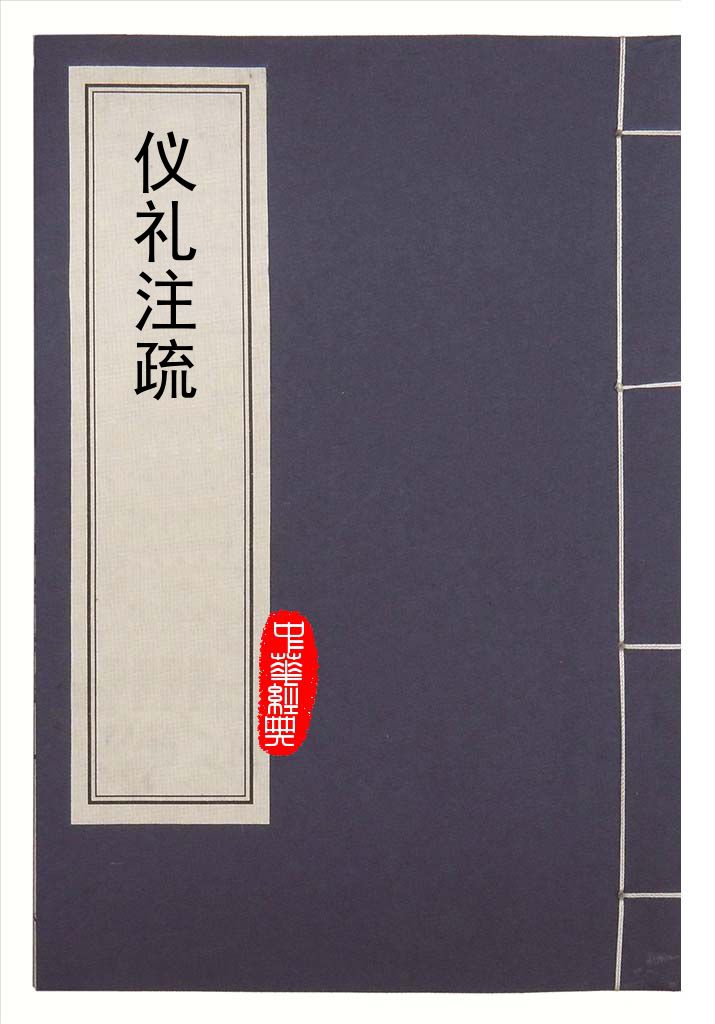
作者: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最近更新 卷五十·有司彻第十七| 2019-04-05 13:58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br> <br>《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br><br>《谷梁》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成为要较《公羊传》为晚。
最近更新 哀公(元年~十四年)| 2019-04-05 13:35

宋史修于元末,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br><br>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后来,袁桷又奏请购求辽、金、宋遗书,虞集也曾奉命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不同,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決」[一],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于公元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又诏修辽、金、宋三史[二],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宋史在纪、传、表、志本已完僃的基礎上[三],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成书。<br><br>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一][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二]元史卷四一顺帝本纪。 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佔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況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br><br>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一]。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熹)为宗。」[二]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鐵木儿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三]。张起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一]。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二]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三]的道学家。宋史的修撰原则是,遵循「先儒性命之说」,「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四]。在这个原则下,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五],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br><br> 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六]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在宋史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牴牾等等。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一三四六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一四八○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一九五八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因此,这次校点宋史,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凡是点不断、读不通而又无法从版本上校正的地方,适当地作了本校和他校工作,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
最近更新 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 2019-04-05 1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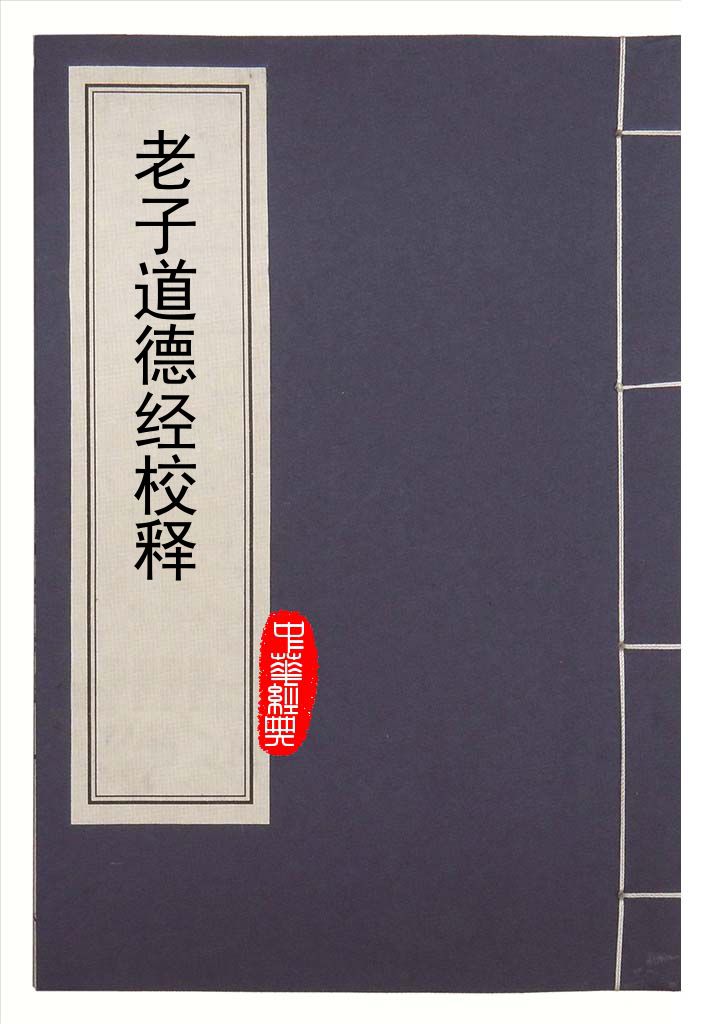
(一)本书在选本方面,以唐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本为主,次取敦煌写本与遂州碑本参订。石本于御注、广明、景福以外,更参考楼正、邢玄、庆阳、磻溪、高翿、赵孟俯诸本。钞本参考柰卷及室町时代钞本。刻本王本除用明和宇惠本外,更参考道藏本、范应元引王本,与道藏宋张太守汇刻四家注本。河上本除用宋刊本外,更参考道藏李道纯道德会元所用章句白本。又如傅、范古本,夏竦古文四声韵所引古老子,及托名王羲之帖本等,均加以批判的选用。 (二)本书在校勘方面,以严可均铁桥金石跋中老子唐本考异所校三百四十九条为主,魏稼孙绩语堂碑录,或正严误,或补严阙,共四十三条,次之。余如纪昀、毕沅、王昶、吴云之校老子,乃至罗振玉之道德经考异,何士骥之古本道德经校刊,凡与碑本校勘工作有关者,无不尽力搜罗,务求去伪存真,使道德经文字得以接近于本来面目。 <br><br> (三)本书在训诂方面,所采旧注有王念孙、孙诒让、俞樾、洪颐烜、刘师培、易顺鼎、马叙伦、陶鸿庆、奚侗、蒋锡昌、劳健、高亨、于省吾诸家;间亦采取日本大田晴轩、武内义雄之说。案语则随文声叙,或出己见,其中有特重声训之处,说本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br><br> (四)本书在音韵方面,以江晋三老子韵读为主,偶有漏失,则以姚文田之古音谐、邓廷桢之双砚斋笔记、李赓芸之炳烛编补之。若刘师培之老子韵表,高本汉之老子韵考,及奚侗,陈柱之说老子古音,则多肊说,其合者取之,不合者弃之。 (五)本书特重楚方言与老子之关系。如四十五章“躁胜寒”,据诗汝坟释文“楚人名火曰燥”。五十五章“终日号而不嗄”,据庄子庚桑楚篇司马彪注“楚人谓唬极无声曰嗄”。七十章“披褐怀玉”,据淮南子齐俗训注“楚人谓袍为短褐大布”。此类之例,说详各章,阅者察之。 <br><br> (六)本书初稿成时,承杨树达先生、任继愈先生校正全书数次,梁启雄、王维诚二先生亦校正其一部分,得益良多。本书即根据诸先生提供之宝贵意见,经数次修改而成。其中如仍有误谬之处,应由撰者自己负责。又以杨树达先生贡献最大,且为其晚年最后之劳绩,应以此书为其纪念。
最近更新 补注| 2019-04-07 1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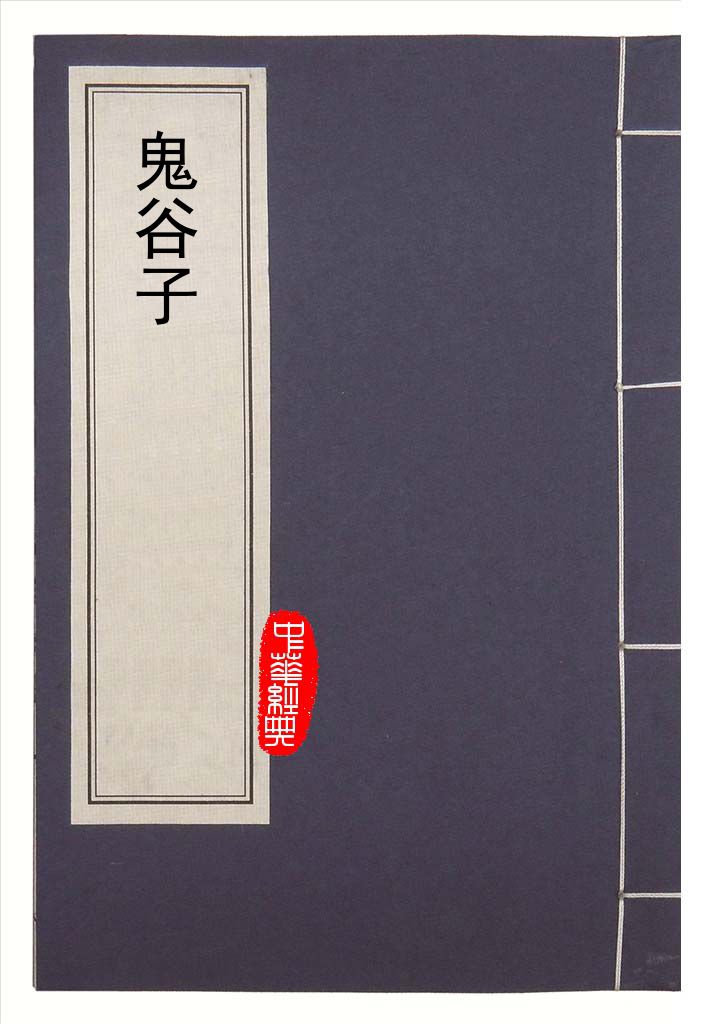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br> <br>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br><br>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br>==============================================================================<br>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br><br>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br><br>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br><br>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 <br><br>《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br><br>《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br><br>此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最近更新 符言第十二| 2019-04-07 2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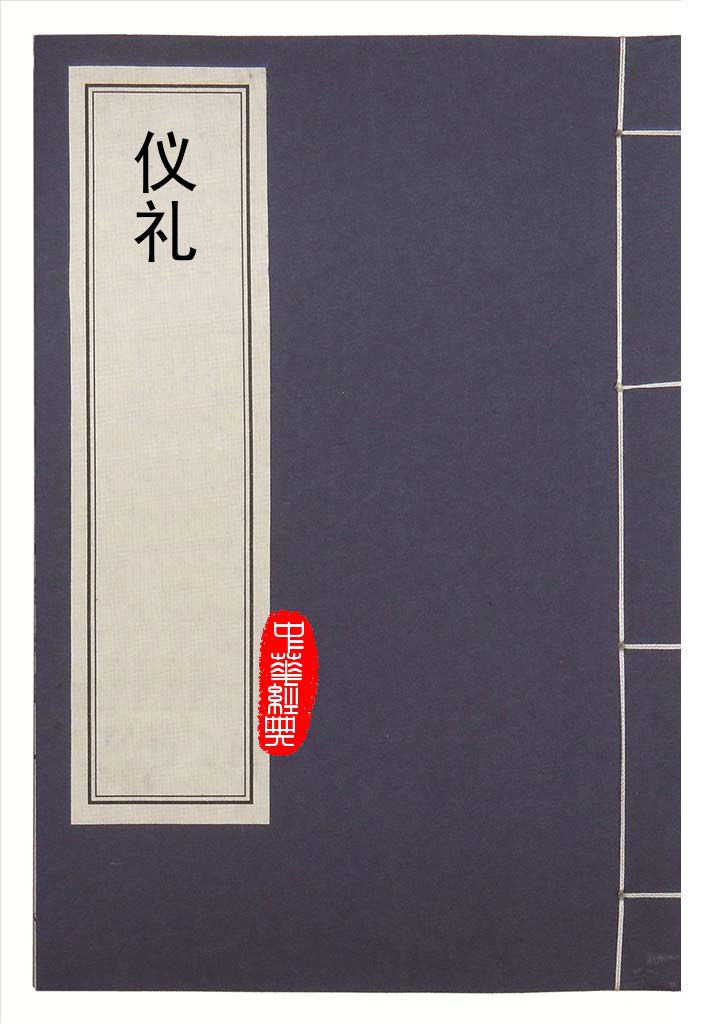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br><br>《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br><br>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br><br>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br><br>《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最近更新 有司第十七| 2019-04-05 1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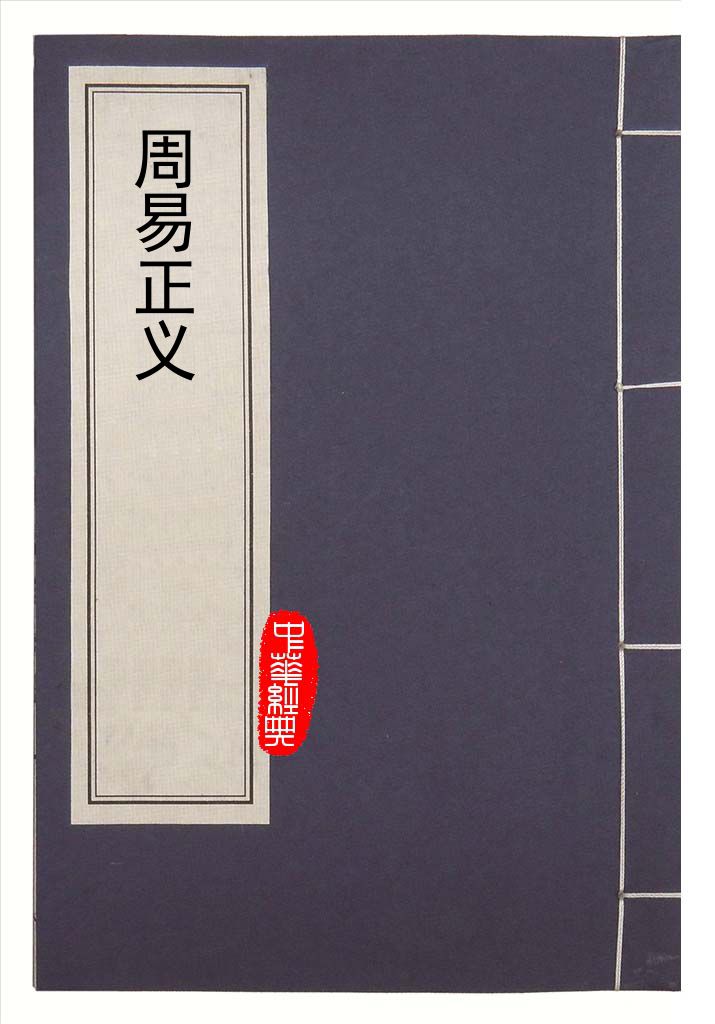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 | 十三经注疏 | 已完结1834 点击
<p>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易》本蔔筮之書,故末派浸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棄漢儒,自標新學。然《隋書·經籍誌》載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冊府元龜》又載顧悅之(按悅之即顧夷之字)《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又申王難顧,是在當日已有異同。王儉、顏延年以後,此揚彼抑,互詰不休。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註而眾說皆廢,故《隋誌》「易類」稱:「鄭學浸微,今殆絕矣。」蓋長孫無忌等作《誌》之時,在《正義》既行之後也。今觀其書如,《復·彖》「七日來復」,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九二「利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詰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雲『時舍』,《註》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天元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註「二四為陰,三五為陽」,則曰「輔嗣以為初上無陰陽定位」,此註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註,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亨於帝,吉』,輔嗣註雲:『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為天帝也」。是雖弼所未註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解註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義,頴達至斥為「狐不首丘,葉不歸根」,其墨守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王註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亦非考證之疏矣。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序》稱十四卷,《唐誌》作十八卷,《書錄解題》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與王韓註本同,殆後人從註本合並歟?<br /> <br /> 作者:(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疏</p>
最近更新 杂卦卷十一| 2019-04-05 1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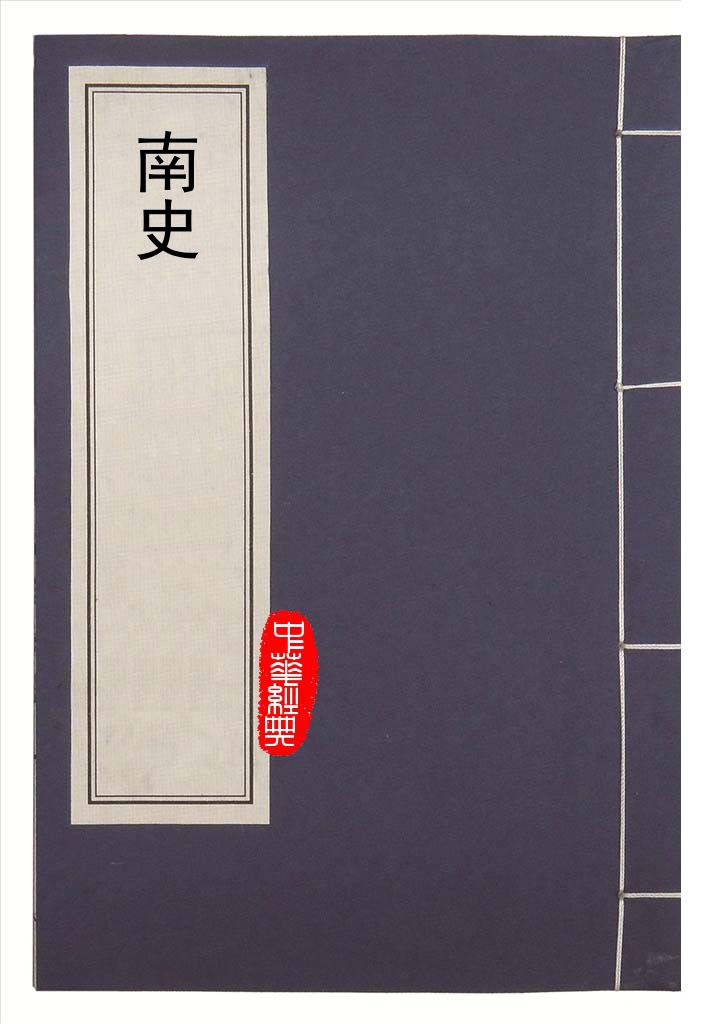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南史起公元四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终公元五八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记述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起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记述北朝魏、北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两书合称南北史。<br><br> 李延寿,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在唐太宗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br><br> 南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隋末,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他被唐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公元六二八年(唐太宗贞观二年)。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虜’,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並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虜」、「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br><br> 李大师本是仿照吴越春秋,採用编年体,没有成书。李延寿在他的基础上,改用史记纪传的体裁,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补充了一些史料,写成南史和北史。公元六五九年(唐高宗显庆四年),这两部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唐高宗对它很重视,曾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已经失传。<br><br> 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这种编纂方法並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就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徵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的党援,享有政治特权,佔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土地。高门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中央或地方任官,三四十岁便可飞黄腾达。大族之间以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膠漆坚固的特权阶層。他们也排斥着庶族地主。「地望」和「婚」、「宦」,是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帜,这些都记载在他们的谱牒里。所以南北朝的大族特别重视谱牒,讲究谱学。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冲击着高门大族,从南北朝到隋末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许多大族地主被革命的农民所镇压,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盘据的地区。<br><br> 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br><br>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挽救自已的颓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的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br><br> 南北史和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相比较,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是长短互见的。八书保存史料较多较详,经过南北史的删节,篇幅仅及原书总和的二分之一,自然不免缺略。它所删掉的,在本纪中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文章。删节以后,叙事部分相对突出,读来比较醒目。可是,也有删所不当删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和思想斗争的重要资料,南北史一则摒棄不録,一则删存无几。在删节过程中,还有由於疏忽而造成的史实錯误,甚至文气不接,辞义晦涩。这些都是这两史在编纂上的缺点。<br><br> 南北史并非单纯节抄八书,它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了不少补充。例如南史补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在循吏、文学、隐逸、恩倖等类传中也补了若干人的整篇传记。北史因魏书不记西魏史事,所以它根据魏澹魏书补了西魏三帝纪,后妃传中补了西魏诸帝后,宗室传中对人关的元魏宗室都增补了资料,此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的纪传中补充史实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有的原传文字无几,增补的部分超出数倍,如南史的恩倖传就是例子。所补史料,也有些價值较高的。例如南史郭祖琛传,通过他所上的封事,揭露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弊政。茹法亮传保存了唐禹之起义的部分史料。巴陵王子伦传和吕文显传记录了宋、齐两代中书舍人和典籤权力膨胀的事例。范缜传增加了他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表现了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北史李弼等人传后,对西魏、北周的军事制度有较详细的记载。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br><br>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br><br> 本书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即商务印书舘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又查对了北京图书舘所藏宋本残卷。版本異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br><br> 除版本校勘外,还参校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通志。因为南北史本是节删八书,它的原则是「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这八部史书当然可以作为校勘的主要根据。而通志的南北朝部分,则基本上是钞録南北史,文字上的異同,对于校正这两部史书也有一定的参考價值。此外,还参考了通鑑、太平御览、通典等书。前人成果利用最多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和张元济、张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记稿本。其他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张熷的读史举正,洪颐煊的诸史考異,李慈铭的南史札记和北史札记等书,也都曾参考。<br><br> 各卷目录基本上保持元大德本原目,只改正了其中若干错误。
最近更新 卷八十 列传第七十| 2019-04-05 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