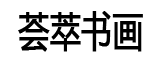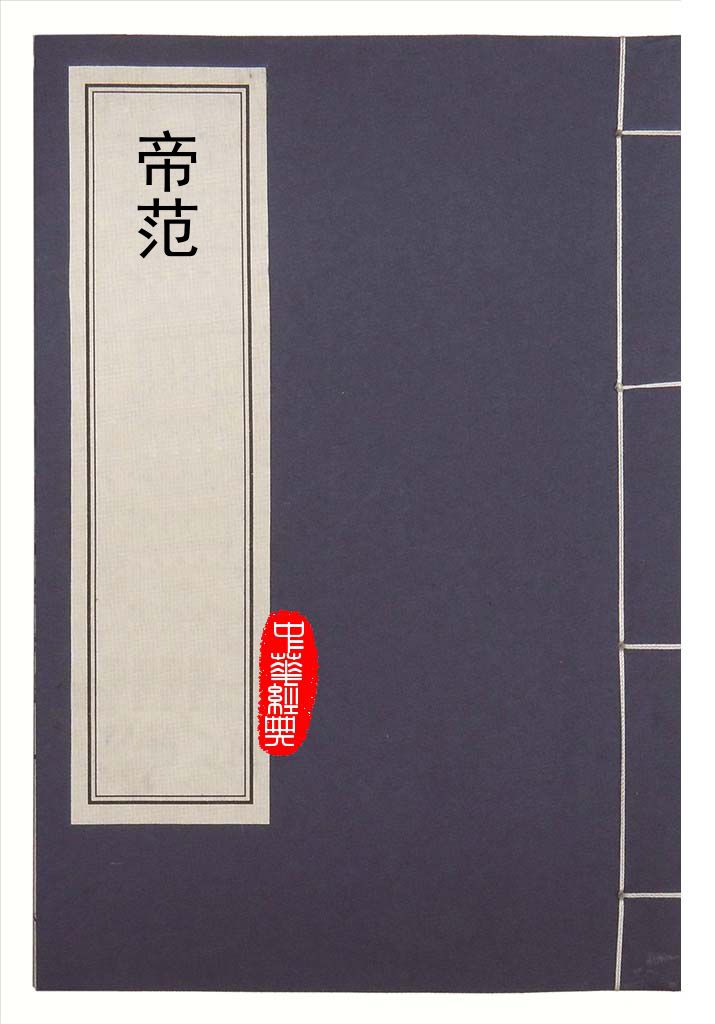兵征凶,圣人万不得已而用之:征伐无道,诛杀暴虐。然而,玩弄兵火者,必自焚。
阅,简也。武,兵事也。《左传》曰:戡乱曰武。古者明王虽享隆平之时,亦未尝不阅武以备不虞,故《周礼》大司马以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大阅者,前期群吏戒众庶修战法也。讲修战法既成,专使大司马掌之,有贼贤害民者,则伐之;暴内陵外者,则坛之;野荒民散者,则削之;负固不服者,则侵之;贼杀其亲者,则正之;放弑其君者,则残之;犯令陵政者,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者,则灭之。故诸侯听命,蛮夷宾服也。坛,音善,与同,废旷之地也。
【原文】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通元真经》云:善治国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夫怨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谓授民以凶之器,纳民于事之危,故号凶器。]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彫;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汉书》主父偃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之谓也。好,乐也。彫,残也。亟,急也。殆,危也。]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刘子》曰: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其辞义大同。言穷兵黩武,人民凋丧,而欲保全,不其难乎?上下危殆,盗贼蜂起,而欲拟弭,亦莫得也。]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故不可常用也。且兵者,守国之备,故不可全除也。故《左传》曰:不备不虞,不足师也。]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左传》曰: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长幼、习威仪也。搜、苗、狝、狩,四时之猎名也。盖古之兵赋出于农,故讲武于农之四时闲隙,以习上下之威仪也。至三年大训,治其兵事,辨其等第、行列、坐作、进退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按:《吴越春秋》越王勾践将伐吴,自谓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见蛙张腹而怒,将有战争之气,即为之轼。其士卒有问于王,曰:君何为敬蛙而为之轼?勾践曰:吾思士卒之怨久矣,而未有称吾意者。今蛙虫无知之物,见敌而有怒气,故为之轼。于是军士闻之,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轼,《尸子》作式,《刘子》作揖。式,犹敬也。式,车之横木。勾践见蛙而俯凭车横木以敬之。《论语》凶服者式之,是己。]徐偃弃武,遂以丧邦。[刘向《说苑》曰: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理?文王遂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修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术。徐偃王将死,曰:古之王者,其有备乎?徐偃王,周穆王时诸侯也。又《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故骃号偃。按:《说苑》术作心。又裴骃《史记集解》引《尸子》文,下有“骃谓号偃。”由此句,注作“故骃号偃,”误。]何则?越习其威,[勾践习衍其兵威。]徐忘其备。[徐偃王忘失其武备。]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上缺以字,引孔子之言以证之也。言不预教练其民,卒驱之以赴敌,是犹委弃之也。又《孙子兵法》曰:兵甲不坚,器械不精,练习不熟,是以其卒与敌也。
与,亦犹弃也。]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易·系辞》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弧,弓也。矢,箭也。世本曰黄帝臣挥作弓,牟夷作矢。]此用兵之机也。[机,要也。
言此乃调用兵旅之机要也。]【译述】军队和武器,是国家用来对付凶乱暴虐的工具。一个国家,虽然领土广大,如果喜好战争,那么人口就一定会减少;尽管秩序安定,如果频繁动武,那么国力就一定要衰竭。人口缺乏就难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力削弱就难以抵御贼寇的践踏侵凌。因此,战争一事,务求慎重,既不能没有,也不能常用,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所以作君王的要在四季农闲之际,不忘讲解和演习军事。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既是为了打猎,也是为了练兵。历史上,越王勾践将要伐吴复仇,苦于找不到机会鼓舞士气。不料偶尔在路上遇到青蛙张腹而怒,于是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征兆。勾践借机行事,以对青蛙表示深切敬意的方式,唤起军心,最终取得了伐吴的胜利。由此可见,只要适逢其时,该战则战,就会扭转乾坤复国兴邦。周穆王时期,有一个叫徐偃王的诸侯,一心只知行仁义之道,不懂得以军事作为防备,别人虽然向他指陈利害,却没有引起重视,结果终因武备松弛而被文王攻灭。徐偃王临死之际,虽痛心疾首,可惜悔之晚矣!为什么勾践明白战争的意义,而徐偃王却忘记武备的作用呢?孔子说:不预先教导和训练百姓,让他们知晓战争的价值,临到不测之时,急忙驱赶他们去迎战,这叫做白白地把人民丢给了敌人。《孙子兵法》也说,军队不强大,装备不精良,练习不熟悉,拿这样的武装去投入战争,也等于是在敌人面前白白送死。所以,只有真正明白战争与武备的含义,才可以退得以守,进得以攻,常居不败,永保太平,这才是战争的深刻价值。
阅武释评《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满足于粗服素食,不去横征暴敛,就不会招致侮辱;后一句是说满足于兵革止息,不去滥兴武事,就不会导致失败。知足也好,知止也罢,其实说的是一码事,即垂拱而治,才会使天下安定,国运长久。
关于战争的利害得失,《老子·三十一章》进一步阐释道:“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君王,不会轻易去使用。..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应该使用的东西,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它,也最好是能淡然处之。胜利了但不要得意,如果得意,就说明是喜好杀人。喜好杀人,就不能顺利地统治天下。吉庆的事情以左为上,凶丧的事情以右为上。偏将军在左边,上将军在右边。这说明是用丧礼的仪式来对待用兵。杀人很多的话,就用悲伤的心情去对待。尽管战胜了,也要用凶丧的礼仪对待。”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酷爱和平的礼仪之邦。从孔子开始,就强调“治国以礼,为政以德。”不仅是儒家学派,先秦时期别的学派,也绝大多数都反对暴力和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试以儒家经典《论语》为例,在《季氏》篇中这样写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墨家则更以兼爱、任贤、节俭和非攻著称于世。在《墨子》一书中,光是《非攻》就有上中下三篇,由此也可知道墨家对战争的厌恶和鄙视。“非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去攻打别的国家。儒家和墨家尽管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要求统治者爱护人民和反对一切战争这个问题上,却又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更为难得的是,墨子不仅在理论上提出“非攻”的主张,而且注重实践,在行动上也竭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如在《公输》中,他就曾以细致周密的防御策略制止了公输盘助楚攻宋的战争,帮助宋国解除了危难。
诸子百家中,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因喜欢刑名法术之学,所以常被人误解为主战派,这其实是很不应该的。韩非固然主张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但这和战争政策其实是两回事。相反,他对那些腐儒用文学来扰乱法律,游侠用勇武来违犯禁令的做法,却表示了极端的否定。《五蠹》中写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连游侠们的逞强斗狠都被认为是导致国家混乱的祸根,韩非又怎么可能张扬战争呢?
那么,是不是用和谈的方式可以解决一切纷争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合纵连横。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必须让历史回到历史那里去。六国的合纵,表面看是战争的手段,其实是为了用战争换取安宁与和平。合纵联盟的形成,其目的是为了防御战争而不是为了挑起战争。我们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个极富理想色彩的假设:如果当时的合纵联盟真正形成一股众志成城牢不可破的力量,就可以有效地箝制强秦的攻伐,并进而有效地维护各国的和平。遗憾的是,六国联盟因其是乌合之众,不战自溃,故尔秦国才敢狼烟再起,横扫东西。因此,就当时形势来说,合众的意义也不能说是消极的。与此相对,连横从本质上看,其意义却主要是积极的。因为连横的结果,是使天下归于一统,真正而且永久地实现了和平,顺应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同样,尽管连横是以“远交近攻”的战争方式来实现的,但它却前所未有地结束了七雄争霸的混乱局面,使长期纷争不休的中国第一次实现了高度的统一。人们习惯于把战争与和平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肤浅的思想。要知道,和平之果的得来,常常须仰仗战争之剑的挥杀。人们更习惯于把战争看作是恶,而认为只有和平才是善。其实,在一定时期,或在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推动人类历史向前不断发展的动力,才是荡涤丑恶扫除污浊换取清平的救世良方。当然,如果视战争为儿戏,把战争变成穷凶极恶的利器和屠杀无辜的法宝,那就不仅谈不上任何进步,反而成了个别丧心病狂的政治家和战争狂人的血腥娱乐。其为害之深,造孽之重,就会触目惊心了!因而,战争一事,小到部落,大到民族,既不能彻底废止,也不能片面张扬。只有用它去止暴,用它去维和,才是正确而明智的态度。
否则,用战争去纵暴逞欲,用战争去破坏和平,则是错误而愚蠢的做法。唐太宗虽然在《帝范》中告诫他的儿子李治(即唐高宗)要慎用战争,自己在和大臣们问答讨论时也反复提醒大家要认识到战争的可怕性,可是承平日久之后,却也无所顾忌地在他的后期推行了一条武力侵略的路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攻打高丽。一个人身居高位而又功成名就之后,就必然会不可理喻地变得固执骄狂起来,这是古今中外一条颠扑不破的普遍规律。唐太宗自然也不能例外。贞观二十二年,已经是他生命倒计时的第二年,唐太宗还是决定要出兵高丽。此时此刻,不用说别人,就是太宗自己,大概也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搞糊涂了大家没什么,但可悲的是太宗把自己也搞糊涂了。他变得那样武断、那样专横,竞至于面对那么多的苦谏也丝毫不为所动。事情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且看一段房玄龄的谏表吧:“高丽国,是边远地方卑贱的族类,不值得用仁义去对待,也不能用正常礼仪去要求它。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它当作鱼鳖一类的动物看待,我们也自然应该对它宽缓简略些。一定要灭掉它,我非常担心它会像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一样拚死反扑。..何况现在当兵的没有一点罪过,却无缘无故地把他们驱赶到战阵之中,置之于锋刀利剑之下,使他们惨烈牺牲,成了孤鸿野鬼,让他们的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着载运棺材的车子掩面哭泣,怀抱尸骨而肝肠寸断,这样足以使阴阳颠倒,乃至破坏了天地之间的谐和之气,这实在是天下的冤屈和悲痛啊!况且,兵器是凶器;战争也是危险的事情。它们都是万不得已时才可以使用的。假设高丽国过去违背了作臣子的礼节,您诛灭它是可以的;假设它曾经侵扰过我们的百姓,您消灭它是可以的;假设它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的祸患,您削除它也是可以的。这几条中如果占有一条,那么您就是一天杀成千上万个人,我们也不必羞愧。现在这三条并不存在,您却让我们自己的军队去劳师袭远,其结果是对内为它过去的国王洗刷了怨恨,对外为新罗报了仇,难道不是所得太少,而损失太多了吗?”太宗虽然为房玄龄这种勇敢正直的精神所深深感动,但他还是一意孤行,终于不顾一切地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又与他的初衷和一贯教导多么大相径庭啊!也许,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矛盾而难解的谜团组成的吧!《左传》曰:“允当则归”,意思是任何事情都应该适而可止。对于战争来讲,就更是这样。因为战争既可以造福,更可以为孽。晚清重臣曾国藩以武功名震朝野,但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却一再强调战争的恶果,因而不厌其烦地警告子弟慎勿介入行伍兵事。在他看来,战争“易于造孽,难以为功”,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人民的罪人,其危切之意,真是再明晰不过了。
一个国家之所以养军队,其实主要是为了战略防备。如果养军队是为了穷兵黩武,对他人构成威胁和侵略,就必然会使戌卒怨愤、国疲人乏,从而把国家和人民推入战祸的深渊。唐太宗的君臣问答,仍然是绝好的例证。《贞观政要》载: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发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实,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士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尅翦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这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啊!而房玄龄在贞观十七年的一段谏词,又恰好是太宗上述思想的延伸。他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唯陛下详察。”陛下怎么样了呢?自然是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劝阻。于是,一场可能的战争被制止了。
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楚汉战争,或许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刘邦之所以终成霸业,项羽之所以乌江自刎,除了策略上的、性格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众多原因,是不是视战争为争夺天下的唯一手段和途径,大概是他们之间结局迥异的最本质区别。诚如外国军事学家所言,战争的核心是哲学而不是武力。无论人们怎么说刘邦入关后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是玩儿装孙子的把戏,但刘邦这样做,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尽管这是一时之策,然而也因此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看看那个项羽吧,杀子婴,戮楚王,烧阿房,屠咸阳,几乎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两相比较,百姓信服谁、拥戴谁,不是昭然若揭吗?二十个世纪之后,毛泽东作诗道:“不可沽名学霸王”,让我们从这朴实而深刻的诗句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