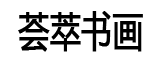督学黄南山先生润玉
黄润玉字孟清,号南山,浙之鄞县人。幼而端方,不拾遗金。郡守行乡饮酒礼,先生观之,归而书之於册,习礼者不能过也。诏徙江南富民实北京,其父当行。先生年十三,请代父往。有司少之,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长。”有司不能夺而从之。至则筑室城外,卖菜以为生,作劳之余,读书不辍。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谢不往。或问之,曰:“渠有一女,当避嫌也。”寻举京闱乡试,授江西训导,用荐召为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广。劾藩臬郡县之不职者,至百有二十人,风采凛然。景泰初,改广西提学佥事。时寇起军兴,先生核军中所掠子女,归者万余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数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卫在万山中,岁苦瘴厉,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忧起复,移湖广,与巡抚李实不合,左迁含山知县。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学,以知行为两轮。尝曰:“学圣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务在读书,制行要当慎独。”盖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为李文毅时勉、薛文清瑄,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万象录天只气,地只质,天地之生万物,如人身生毛发,任其气化自然也。而人独有心中一窝气,寓得理而灵,故曰心神。然太虚中亦有一团气,灵如人心者,则曰天神。
汴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运之易集也。
道有体用,体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谓德?知仁、圣义、中和是也。何谓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循理而行。
在天为理,与天常存,在人为性,气散则亡。
告子若曰“生理之谓性”,便不起人争端。天地间只是生气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总谓之仁。是仁即系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气质之性,即告子生之谓也。故张子曰:“君子弗性也。”
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国之命,若长平坑卒,一国之命也,气数也。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间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势,古今制度,必须考视而知,难意度也。
程、张所谓心,皆指其虚灵之气而言,气本寓理为性,理从气发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气也。
天地间生生不息为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间断便是不仁。
孔门所教所学,皆於用处发明,而体在其中。盖理是道之体,事是道之用。孝弟见於日用,只从仁上发出来。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学者骛於高远,不尽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论心论性,却全不识道。
教学者於自己体认性情发见处,便能知道。
古者士农工商,各一其业,子孙世守,而民志定。今也农工商之贪黠者,皆奔兢仕途,而谋吏胥出身,往往资其贪黠,卒获仕途以终其身,所以滥溢铨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为今之计,莫若自民间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约计藩臬郡县司吏额,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为藩臬阃司之吏,中等为各郡吏,下等为州县吏。三年考满,送礼部会试,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门历役三年,都试出身,则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贪黠之风矣。
《大学》之道,问学之宏规;《论语》之言,践屐之实理;《孟子》七篇,扩充之全功;《中庸》一书,感化之大义。《大学》一书,《六经》之名例也;《中庸》一书,《六经》之渊源也。
穷理者道之体斯明,尽性者道之体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达,故邵子曰:“非道而何?”经书补註
格物格字,当训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过於家国天下。人之所学,莫非身心家国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万物皆备於我,则物理具於吾心。学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训为至,则为物至而后知,至不成文义也。(《大学》)
告曾子以道言,谓一理贯万事,理即体,事即用。告子贡以学言,谓一心贯万理,心者气之灵,理者心之德。
一日克己复礼,一日以成功之大纲言,四勿以日日用功之节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发,日日要当克胜他,及至一日尽克胜了,而复却好地方,则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补传“一旦豁然贯通”,即此一日义同。天理寓於人曰性,犹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无不善,而人之气禀有清浊;泉无不洁,而川之泥质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气之清浊未甚见,及其长而习於善,则清者愈清,习於恶,则浊者愈浊。如川之始达,泥之澄浑未甚分,及其远也,积於沙者,则澄者愈澄,汩於泥者,则浑者愈浑矣。故性近习远。(以上《论语》)
浩气是心窝中一点虚灵之气,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则心无愧怍而天理纯全,斯可识浩然之气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此浩气塞於天地之间也。
义者人心之裁制,气之主也,即所谓志帅也。道者事理之当然,气之行也,即所谓道路也。
万物皆备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处物合宜,即义也。此之谓体用。(以上《孟子》)
《尧典》以亲九族,即齐家也。止谓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玄,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人道竭矣。岂有外姓之谓族乎?故《尔雅》别外姻曰母党,妻党。(《书》)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则有是理。如视必明,听必聪,色必温,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即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视思明,德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即思也。盖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体,故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诗》)
古者诸侯之别子之子孙,嫡派为大宗,其庶子为小宗。若小宗绝,不为立后,惟大宗绝,则以支子立后。盖大宗是尊者之统,不可绝也。今制大宗绝立后,小宗绝不立后,奈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绝,皆令过继,只是争取财产尔。
古昔吉服,杀缝向外,以便体;后王致饰,杀缝向内为吉服,以外削外缉者为凶服。
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东,祭时佐食取黍稷,祝取觯祭於苴,而祭毕弃之,即老氏所云刍狗也。今朱子家礼,乃束茅置沙于馔食前酎酒,似与古礼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公为尸,今之神有土木偶及遗像,皆古人立尸之遗意欤?(以上《仪礼》)
文毅罗一峰先生伦
罗伦字彝正,学者称一峰先生。吉之永丰人。举成化丙戌进士,对策大廷,引程正公语,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执政欲节其下句,先生不从。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会李文达夺情,先生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数日,始上疏历陈起复之非,为君者当以先王之礼教其臣,为臣者当据先王之礼事其君。疏奏遂落职,提举泉州市舶司。明年召还,复修撰,改南京,寻以疾辞归,隐於金牛山,注意经学。
《周易》多传註,间补己意。《礼记》彙集儒先之见,而分章记礼,则先生独裁。《春秋》则不取褒贬凡例之说,以为《春秋》缘人以立法,因时以措宜,犹化工焉,因物而赋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犹以画笔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赠左谕德,谥文毅。先生刚介绝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其论太刚则折,则引苏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刚尔,折不折天也。太刚乎何尤?为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贫,日中不能举火,而对客谈学不倦。高守赠以绨袍,遇道殣,辄解以瘗之。尝欲倣古置义田,以赡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钱,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执事且不可取,何所用与?”谢而弗受。冻馁几於死亡,而一无足以动於中。若先生庶几可谓之无欲矣。先生与白沙称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辙,学非白沙之学也,而皭然尘垢之外,所见专而所守固耳。章枫山称:“先生方可谓之正君善俗,如我辈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语要子路论为国,而其言不让,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让乎?登降作止饮食不辞焉,人皆以为非也,荣以爵而不辞焉,人不以为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
伯恭居丧授徒,子静极以为非,今日便子静在,恐亦不敢以为非也。
居丧须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无路分说也。
进善无足处,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当。称善虽是美事,然必见得透,恐为伪人所罔。
所以为圣贤,不必删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群圣,以垂宪万世也。不过求之吾心,致慎於动静语默、衣服饮食、五伦日用,以至辞受取舍、仕止久速,无不合乎圣贤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视人犹己,以义处己,不以义处人,非君子之道也。
流俗虽不美,而天下未尝无正人,天下未尝无正论,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
君子之学,持静之本,以存其虚,防动之流,以守其一。虚则内有主而不出,一则外有防而不入,则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则我之所以为我者,非人也,天也。
或曰刚折而柔存,此非知刚者也。天不刚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尝坠,不刚者存而柔者堕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刚而水柔,不刚者存而柔者去乎?齿之折者,刚之无本者也,发附於头颅,头颅存而毛发去者何也?
诚曷终乎?土可入,诚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诚曷不息也?所谓生也,守之以死,死则终,诚不可得而息也。
所见专则守固。
与其以一善成名,宁学圣人而未至。
文懿章枫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华兰谿人。成化丙戌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与同官黄仲昭、庄昶谏上元烟火,杖阙下,谪知临武。历南大理评事,福建按察司佥事,考绩赴吏部,乞休。宰尹旻曰:“不罢软,不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罢软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视民如伤,某贪酷多矣。年虽未艾,鬚鬓早白,亦可谓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进,讲学枫木菴中,学者因曰枫山先生。弘治中,起为南京祭酒,会父丧,力辞。廷议必欲其出,添设司业,虚位以待之。终制就官,六馆之士,人人自以为得师。正德初致仕。转南京太常、礼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礼部尚书致仕。是岁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赠太子太保,谥文懿。其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传授,故表?洞澈,望之庞朴,即之和厚,听其言,开心见诚,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烛照数计,无不验也。以方之涑水,虽功业不及,其诚实则无间然矣。金华自何、王、金、许以后,先生承风而接之,其门人如黄傅张大轮、陆震、唐龙、应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传云。《文懿章枫山先生懋》人形天地之气,性天地之理,须与天地之体同其广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谓之人。学者须大其心胸,盖心大则万物皆通。必有穷理工夫,心纔会得大。又须心小,心小则万理毕晰。必有涵养工夫,心纔会得小。不至狂妄矣。
或劝以着述,曰:“经自程、朱后不必再註,只遵闻行知,於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
《桃符诗》:“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须茶垒卫门庭。”每讲“伯夷、叔齐饿首阳之下,民到於今称之”之语,便自警拔。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后政事可举。
惟唐、虞、三代皆圣人致中和而参赞,下此一泰一否,为气运所推荡耳。
穷理,自进退辞受之节,分明不苟始。
居敬於专一上见功。
应璋问学,先生曰:“勉斋真实心地,刻苦工夫,八字尽之矣。”
遗事诸子皆亲农事,邑令来见,诸子辍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检笞之,知而请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尔不识,又何罪焉!”太宰唐渔石出入徒步,人以为言,渔石曰:“枫山先师致政归,祇是步行。自后朴菴拯、竹涧潘希曾两侍郎俱守此礼,吾安敢违耶?”
枫山祖居渡渎,距城十五里,当事至兰谿者,必出城访之。至则一饭鶪黍数豆,力不能辨,多假借於族人。其后迁居城中,小楼二间,卑甚。先生宴坐其间,每作文时,绕行室中,其冠往往触樑垫角,先生不知也。
先生田祇二十亩,而家人十口,岁须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当其半,则以麦屑充之。
宅后为天福山,一日勾人者过其门,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为先生家匿之,先生即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从后门去。先生与夫人略不动色。
每岁宴其门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餕也。两人其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专一席。若门人续至,专席已罄,则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质朴略相似。先生闻其归家,当有赢俸,即为不乐。朴菴亦有惭色。
原学
人生而静之谓性,得乎性而无累於欲焉之谓学。学在於人,而於性未尝加,不学在於人,而於性未尝损。学有纯正偏驳,而於性未尝杂,性本不学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学。性之动於欲也,学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顾戕夫性,学之失其原也。盖人之性也,即天之命也,於穆不显,命之本体,而四时五行,万化出焉;至静无感,性之本体,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体藏於寂,妙用通於感,运之於心,为思虑,发之於身,为貌言视听,施之於家,为父子昆弟,措之於国与天下,为君臣上下、礼乐刑政。
以性为有内也,何性非物也?以性为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体,则意可诚,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齐,国治而天下平也。据此之谓德,履此之谓道,学此之谓学,勉之为贤,安之为圣。尧曰“执中”,明其体之无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体之无所杂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诚”,孟子曰“尽心”,圣学相传,千古一脉,一性尽而天下无余事,天下无余学也。
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后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胜之者,学之不明,性之未尽也。老氏以无名为天地之始,无欲观人心之妙,无为为圣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则又生其心於无所住,四大不有,五蕴皆空,其道以性为心之体,吾惟修吾心炼吾性而已,明吾心见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学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於天地万物为刍狗,为幻化,弃人伦遗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国家焉。今之学则又异於是矣。
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沦浃而不可解,传训诂以为名,夸记诵以为博,侈辞章以为靡,相矜以智,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身心性命竟不知为何物。间有觉其缪妄,卓然自奋,欲以行能功实表见於世,则又致饰於外,无得於内,莫不以为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齐家也,可以治国平天下也,又莫不以为吾不学佛、老之梦幻人世,遗弃伦理也。然要其所为,不过为假仁袭义之事,终不足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去圣学也远矣。犹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见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见吾人所为,其不窃笑者几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吾闢,不可得也,暇闢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尝一息泯没,而圣学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笃行之,一切气禀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真静之体,以立吾心之极。惩忿惩此也,窒欲窒此也,改过改此也,迁善迁此也。不为佛、老之虚无,不为俗学之卑琐,斯为圣学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体也”,不能戒惧慎独,以求必得,而欲以虚悟入,则意见之障,终非自得。纵使谈说得尽,亦与训诂、记诵、辞章、功利者等耳。而何以为学也?
郎中庄定山先生昶
庄昶字孔暘,号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与同官章枫山、黄味轩谏鳌山,杖阙下,谪判桂阳。改南京行人司副,遭丧。服阕,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琼山丘浚嫉先生不仕,尝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彼不读祖训乎?盖祖训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浚为大学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长揖刀 ,遂补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寻病,迁延不愈。又明年,告归。丁巳,考察,尚书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为之骇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郎中庄定山先生昶》先生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而於所谓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盖功未入细,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后,流传多是此种学间。其时虽与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不知其后问林缉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即如出处一节,业已二十年不出,乃为琼台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郎中庄定山先生昶》先生殊不喜孤峰峭壁之人,自处於宽厚迟钝,不知此处却用得孤峰峭壁着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处平生大分,顾令儿女辈得专制其可否耶?”霍渭谓:“先生起时,琼台已薨。”是诬琼台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门,九月入京朝见,琼台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谓起时已卒哉?况是时徐宜兴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琼台语人“我不识所谓定山也”,则其疾之至矣,安得谓诬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见之诗,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是也。唐之白乐天喜谈禅,其见之诗者,以禅言禅,无不可厌。先生之谈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意象跃如,加於乐天一等。钱牧斋反谓其多用道语入诗,是不知定山,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郎中庄定山先生昶》圣人之道贵无言,而不贵有言。言则影响形,而无言则真静圆融,若愤也而真见,若冥也而真趣,若虚寂也而真乐。彼以天得,而此以天与,极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圣人不贵有言。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则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尽,吾於父母之形为徒受矣。
浙人余中之过溪云,以皇极经世之学授余。读其书至三天说,所谓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时日,而后富寿,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后贱贫,以至水陆舟车之所产,东西南北之所居,精粗巨细之事,无不皆然,而至所谓福善祸淫,略无一二。余虽口唯其义,而心实不敢以为学也。圣贤之学惟以存心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则莹然澄彻,广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听,言动一循乎礼,好恶用舍,各中乎节。
屈原长於骚,董、贾长於策,扬雄、韩愈长於文,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长於数,迁、固、永叔、君实长於史,皆诸儒也。朱子以圣贤之学,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书》、《五经》、《纲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数之学,又皆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者讲明订正,无一不至,所谓集诸儒之大成,此也。岂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
《六经》莫大於《易》,而《易》有阴阳也。方其无言也,易具於心,浑然无为;及其有言,则孰为阴?孰为阳?而阴阳之授受,皆传之纸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纸上而《易》自散也。《四书》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无言也,中庸具於心,噩然无名,及其有名,则孰为性?孰为道?孰为教?而性道教之授受,皆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乱矣。《中庸》非乱也,口耳而《中庸》自乱也。《诗》、《书》、《礼》、《乐》、《春秋》、《论》、《孟》,莫不皆然。心非静,则无所敛,主乎静者,敛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则无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乱也;理非穷,则无所考,穷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
往年白沙先生过余定山,论及心学,先生不以余言为谬,亦不以余言为是,而谓余曰:“此吾缉熙林光在清湖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诋陈为禅者,见夫无言之说,谓无者无而无。然无极而太极,静无而动有者,吾儒亦不能无无也。但吾之所谓无者,未尝不有,而不滞於有;禅之所谓无者,未尝有有,而实滞於无。禅与吾相似,而实不同矣。
道无不在,一大浑沦者,散在万物。散在万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众人则不知也。
杨、墨之害,甚於申、韩,佛、老之害,过於杨、墨。科举之学,其害甚於杨、墨、佛、老。为我、兼爱虚无、寂灭,盖足闢矣。至於富贵利达,患得患失,谋之终身,而不知反者,则又杨、墨、佛、老之所无也。属联比对,点缀纷华,某题立某新说,某题立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五经》、《四书》择题而出,变《风》变《雅》,学《诗》者不知,丧弔哭祭,学《礼》者不知,崩薨葬卒,学《春秋》者不知。呜呼!此何学也?富贵而已,利达而已,觊觎剽窃而已。朱子谓庐山周宜榦有言,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三十年科举始得。盖已深恶之矣。
天地万物,吾一体;窗草不除,皆吾生意;元会运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颜、曾、思、孟,皆吾人物;《易》、《书》、《诗》、《礼》、《春秋》,皆吾《六经》;帝力何有,太平无象,皆吾化育。
天之生圣贤,将为世道计也。或裁成以制其过,或辅相以补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经》,朱子之於传註,唤醒聋瞶,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风移,学者执於见闻,入耳出口,至於没溺而沦胥之者,非制其过可乎?
侍郎张东白先生元祯
张元祯字廷祥,别号东白,南昌人。少为神童,以闽多书,父携之入闽,使纵观焉。登天顺庚辰进士第,入翰林为庶吉士。故事教习唐诗、晋字、韩、欧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关、闽之书读之。授编修。成化初,疏请行三年丧。又言治道本原在讲学、听治、用人、厚俗,与当国不合,移病归,家居二十年,益潜心理学。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进左赞善,上疏劝行王道。陞南京侍讲学士,终养。《侍郎张东白先生元祯》九年,召修《大明会典》。进翰林学士,侍经筵,上注甚,特迁卑座,以听其讲。丁忧丧毕,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为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极图说》、《西铭》、《定性书》、《敬斋箴》,宜将此书进讲。上因索观之,曰:“天生斯人,以开朕也。”武宗即位,进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既得君,尝以前言往行非时封进,不知者以为私言也。孝宗晏驾,为人指谪,先生亦不辩。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禀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已先发阳明“心即理也”之蕴。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随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动者存,不随感而纷。”已先发阳明“未发时惊天动地,已发时寂天寞地”之蕴。则於此时言学,心理为二,动静交致者,别出一头地矣。《侍郎张东白先生元祯》斯道在天地,不患践之不力,所患知之弗真。
萧宜翀蚤游聘君之门,友克贞、公甫、居仁诸子,不饰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诡冠服於吕縚象佩,不纵浮谈於太极。
此道自程、朱后,所寄不过语言文字,循习既久,只形诸文字,而言语殊不之及。形诸文字,纔能执笔,即於性命之奥,帝王之略,极力描写,不以为异。若言语间有及之听者,虽面相隆重,退即号笑之曰:“此道学。”又或公排摈之曰:“此伪学。”士风一至於是。然实由言语者所谈非所见,所见非所履故也。吾人致力於大本,须灼见外教同中有大不同处。此理在天地间,如今造版籍粮册相似,有总有撒。止知囫囵一大块,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略窥影向,便尔叫噪,不复致详、致谨,反谓得人所未得真乐。鄙礼法为土苴,嗤简策为糟粕,卒至颠瞀老死。大抵实有此者,气象自别,语言动静,何莫非此。若不养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跷蹊,不差异,不高远,不粗率,不放肆,彼言动之跷蹊、差异,或务为高远、粗率、放肆者,则其人之能有此与否,可知已。
天地所以相播、相荡、相轧、相磨,昼夜不息者,其心无他,惟在生物而已。虽其雷霆之震击,霜雪之凋残,亦所以破其顽而禁其盛,非心乎杀之也。人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续,然实皆得是生物之心以为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则是身无以生矣。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间,本无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则不能无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不能无,由是诱之以声色之纷华,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乐之发,遂不能无私焉。身既有私,则此心或为之蔽,而天理渐以泯矣。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随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动者存,不随感而纷。
布政陈克菴先生选
陈选字士贤,台之临海人。天顺庚辰试礼部,丘文庄得其文,曰:“古君子也。”置第一。及相见而貌不扬,文庄曰:“吾闻荀卿云,圣贤无相,将无是乎?”授监察御史。罗一峰论夺情被谪,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见,先生曰:“非也。人臣觐君,服视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风裁,而贪墨望风解绶。已督学南畿,一以德行为主。试卷列诸生姓名,不为弥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学宫,诸生分房诵读,入夜灯火萤然,先生以两烛前导,周行学舍,课其勤惰,士为之一变。成化初,改中州提学。倖奄汪直巡视郡国,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趋拜,先生独长揖。直怒曰:“尔何官,敢尔?”先生曰:“提学。”愈怒曰:“提学宁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学宗主斯文,为士子表率,不可与都御史比。”直既慑其气岸,又诸生集门外,知不可犯,改容谢曰:“先生无公务相关,自后不必来。”先生徐步而出。转按察使。归奔母丧。丧毕,除广东布政使。肇庆大水,先生上灾伤状,不待报,辄发粟赈之。市舶奄韦眷横甚,番禺知县高瑶发其赃钜万,都御史宋旻不敢诘。先生移文奖瑶,眷深憾之。番人贸货,诡称贡使,发其伪,逐之外;使将市狻猊入贡,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诬先生党比属官,上怒,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巡按御史徐同爱共鞫。两人欲文致之,谓吏张褧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为诬。褧曰:“死即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书入,诏锦衣官逮问,士民数万人夹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
友人张元祯殓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祯曰:“公平生清苦,殓以时服,公志也。”张褧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诖误触法,为选罢黜,实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选,以厚贿啗臣,令扶同陷选。臣虽胥徒,安敢欺昧心术,颠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诱,嗾行等逮臣於理,弥日拷掠,身无完肤。臣甘罪籲天,终无异口。行等乃依傍眷语,以欺天听。选刚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门万里,孰谅其冤?臣以罪人,摈斥田野,百无所图,敢冒死鼎镬者,诚痛忠廉之士,衔屈抑之冤,长谗佞之奸,为圣明之累也。”奏入不报,第以他事,罢眷镇守。正德中追赠光禄寺卿,谥恭愍。先生尝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论《易》专主传义,一无异同。以克己求仁为进修之要,故自号克菴。读书不资为文辞,手录格言为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斋沐,引使者於庭,而拜而遣。子刘子曰:“由张东白之事观之,非平日安贫守道之意,彻乎表?,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张褧之事观之,非在官赏罚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见先生存诚之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