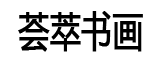通政张东所先生诩张诩字廷实,号东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进士第。养病归,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户部主事。寻丁忧,累荐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又辞,一谒孝陵而归。卒年六十。
白沙以“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其观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观此则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论道,至精微处极似禅。其所以异者,在“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而已。禅则并此而无之也。奈何论者不察,同类并观之乎!
文集儒有真伪,故言有纯驳。《六经》、《四书》以真圣贤而演至道,所谓言之纯,莫有尚焉者矣。继此若濂、洛诸书,有纯者,有近纯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经书,而启万世之蒙,世诚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圣绝言湮,着述家起,类多春秋吴、楚之君,僭称王者耳,齐桓、晋文,假名义以济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驳乎,无足取也。
其蓁芜大道,晦蚀性天,莫甚焉。非荡之以江海,驱之以长风,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东南,倡道四十余年,多示人以无言之教,所以救僭伪之弊,而长养夫真风也。其?言曰:“孔子,大圣人也,而欲无言。后儒弗及圣人远矣,而汲汲乎着述,亦独何哉!虽然无言二字亦着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则於斯道思过半矣。然则《六经》、《四书》,亦剩语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劝先生以着述为事,而以缺着述为先生少之者,盖未之思耳。今则诗集出焉,而人辄以诗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辄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之目,而能得神骏於骊黄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诩诚惧夫后修者,复溺於无言以为道也,因摭先生《文集》中语,倣南轩先生《传道粹言》例,分为十类而散入之。其间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业之着,修为持治之方,经纶斡运之机,靡不灿然毕具。辑成,名曰《白沙先生遗言纂要》,凡十卷。庶观者知先生虽寻常应酬文字中,无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无非至教,盖可触类而长焉。由是观之,先生虽以无言示教,而卒未尝无言,是以言焉而言无不中,有纯而无驳,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圣经而补贤传矣。(《白沙遗言纂要》《序》)
昔吕原明尝称:“正叔取人,专取有行,不论知见。”又说:“世人喜说某人只是说得。”又云:“说得亦大难。”而以为二程学远过众人在此。夫知之真,则守之固,不真而固,冥行而已矣,梦说而已矣。吾恐其所谓介者,非安排则执滞,抑何以得乎无思无为之体,执乎日往月来之机,通乎阳舒阴惨之变化,神之心而妙之手,以圆成夫精微广大之道也哉!(《介石记》)予少从先君宦游临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烟暮雨之间,千态万状,可数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随风力强弱而变化,可数十丈。鹦燕之歌吟,鱼虾之潜跃,云霞之出没,不可具状。则境与心得,既块然莫知其乐之所以。稍长,读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杨柳风来面上吹”之句,则心与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岁养之余,专静,久之理与心会,不必境之在目;情与神融,不必诗之出口。所谓至乐与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柳塘记》)
子思所谓“至诚无息”,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意,全体呈露,妙用显行,惟孔子可以当之。在学者则当终日乾乾也。至於“心无所住”,亦指其本体。譬如大江东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体人人皆具,不以圣丰而愚啬,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为圣人可学而至也,学者不可以不勉也。范书格物,真阴阳不住之说,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为守约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复乾亨》)
士之所守,义利毫末之辨,以至死生趋舍之大,实在志定而守确,坚之一字不可少也。至於出处无常,惟义所在,若坚守不出之心以为?,斯孔子所谓果哉也。(《复曹梧丹》)
天旋地转,今浙、闽为天地之中,然则我百粤其邹、鲁与?是故星临雪应,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应矣,於焉继孔子绝学,以开万世道统之传,此岂人力也哉!若吾师白沙先生,盖其人也。先生以道德显天下,天下人向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称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资禀绝人,幼览经书,慨然有志於思齐,间读秦、汉以来忠烈诸传,辄感激齎咨,继之以涕洟,其向善盖天性也。壮从江右吴聘君康斋游,激励奋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归,杜门独扫一室,日静坐其中,虽家人罕见其面。如是者数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於是自信自乐。
其为道也,主静而见大,盖濂、洛之学也。由斯致力,迟迟至於二十余年之久,乃大悟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一真万事,本自圆成,不假人力。其为道也,无动静、内外、大小、精粗,盖孔子之学也。濂、洛之学,非与孔子异也。《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诚之,其理无二,而天人相去则远矣。由是以无思无为之心,舒而为无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无弗获,有弗感,感无弗应,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绝,不以目而能书,不以心而能诗,天章云汉而谐金石。胡为其然也?盖其学圣学也,其功效绝伦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圣贤,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圣功莫能也。圣功叵测,其可以穷达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韩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谓也。先生虽穷为匹夫,道德之风响天下,天下人心,潜移默转者众矣。譬如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盖不知也。其有功於世,岂下於抑洪水驱猛兽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讳献章,字公甫,别号石斋,既老,曰石翁。吾粤古冈产也。祖居新会,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称之。其世系出处,见门人李承箕《铭》、湛雨《状》者详矣。诩特以天人章应之大者表诸墓,以明告我天下后世,俾知道统之不绝,天意之有在者,盖如此。(《白沙先生墓表》)
给事贺医闾先生钦
贺钦字克恭,别号医闾。世为定海人,以戎籍隶辽之义州卫。少习举子业,辄鄙之曰:“为学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进士第,授户科给事中,因亢旱上章极谏,谓“此时游乐,是为乐忧。”复以言官旷职,召灾自劾。寻即告病归。白沙在太学,先生闻其为己端默之旨,笃信不疑,从而禀学,遂澹然於富贵。故天下议白沙率人於伪,牵连而不仕,则以先生为证。构小斋读书其中,随事体验,未得其要,潜心玩味,杜门不出者十余年,乃见“实理充塞无间,化机显行,莫非道体。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实理,吾人之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谓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閈\间,冠婚丧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纯熟,心迹相应,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边将诈诱杀为阵获者,见先生即吐实曰:“不忍欺也。”城中乱卒焚劫,不入其坊。先生往谕之,众即罗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诚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悬其像於书室,出告反面。而白沙谓先生笃信谨守人也,别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犹未以冻解冰释许之。盖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鲁男子之学柳下惠与?
给事贺医闾先生钦言行录
门人于衢路失仪,先生曰:“为学须躬行,躬行须谨隐微。小小礼仪尚守不得,更说甚躬行,於显处尚如此,则隐微可知矣。”
门人有居丧而外父死,或曰:“礼,三年之丧不弔。”先生曰:“恶是何可已?服其服而往哭之,礼也。”(言不易三年之服。)
善恶虽小,须辨别如睹黑白。
教诸女十二条,曰安详恭谨,曰承祭祀以严,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礼,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抚婢仆以恩,曰接亲戚以敬,曰听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诚,曰务纺织以勤,曰用财物以俭。
有来学者,言学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学,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学?”
问:“静极而动者,圣人之复,岂常人之心无有动静乎?”曰:“常人虽当静时亦不能静。”此理无处不有,无时不然,人惟无私意间隔之,则流行矣。
为学先要正趋向,趋向正,然后可以言学。若趋向专在得失,即是小人而已矣。
政事学问原自一贯,今人学自学,政自政,判而为二,所学徒诵说而已,未尝施之政事。政事则私意小智而已,非本之学问也。故欲政事之善,必须本之学问。
白沙后有书来,谓其前时讲学之言,可尽焚之,意有自不满者。圣人之法,细密而不粗率,如人贤否,一见之,便不言我已知其为人,必须仔细试验考察之。今人一见,便谓已得其实,真俗语所谓假老郎也。为学之要,在乎主静,以为应事建功之本。读书须求大义,不必缠绕於琐碎传註之间。
骄惰之心一生,即自坏矣。
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乡之俗,有一家之俗,为士者欲移易之,固当自一家始。
今人见人有勉强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诚实。”我尝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饮酒,此正矫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饮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为诚实不造作,可乎?
世教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则流於粗浅,一则入於虚无。
有以私嘱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谓门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劝之;渠是拖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
世风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与俗违拗,方能去恶为善。
静无资於动,动有资於静,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静物,便皆自足,不资於动物。如鸟兽之类,便须食草栖木矣。故凡静者多自给,而动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静;而躁动营营者,必多贪求也。
人於富贵之关过不得者,说甚道理。
今之读书者,只是不信,故一无所得。
事之无害於义者,从俗可也,今人以此坏了多少事。
天地间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太过不及,遂流於恶。如丧葬之礼,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后世之侈,皆流於恶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
吏目邹立斋先生智
邹智字汝愚,号立斋,四川合州人。弱冠领解首,成化丁未举进士,简庶吉士。孝宗登极,王恕为吏部尚书,先生与麻城李文祥、寿州汤鼐,以风期相许。是冬值星变,先生上言:“是皆大臣不职,奄宦弄权所致。请上修德用贤,以消天变。”不报。又明年,鼐劾阁臣万安、刘吉、尹直。中官语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将并劾中官。”中官避匿。寻有旨,安、直皆免。先生与文祥、鼐日夜歌呼,以为君子进小人退,刘吉虽在,不足忌也。吉阴使门客徐鹏、魏璋伺之。会寿州知州刘概寓书於鼐,言:“梦一叟牵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国姓,此国势濒危,赖公复安之兆也。”鼐大喜,出书示客。璋遂劾鼐、概及先生,俱下诏狱。先生供词:“某等往来相会,或论经筵,不宜以寒暑辍讲;或论午朝,不宜以一事两事塞责;或论纪纲废弛;或论风俗浮薄;或论民生憔悴,无赈济之策;或论边境空虚,无储蓄之具。”议者欲处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获免。谪广东石城吏目。至官,即从白沙问学,顺德令吴廷举於古楼树建亭居之,扁曰“谪仙”。其父来视,责以不能禄养,箠之,泣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举治其丧。方伯刘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贤之。
吏目邹立斋先生智言行录
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谓曰:“三代而下,人臣不获见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请对面陈时政之失,上许更张,然后受职。”又谓汤鼐曰:“祖宗盛时,御史纠仪得面陈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间隔也。请修复故事,今日第一着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识者憾之。
吏目邹立斋先生智奉白沙书
克修书来,问东溟几万里,江门未盈尺,妄以“道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则作者为郢书,解者为燕说矣。京师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处,是陈太丘、柳士师以上规模,晚生小子脚根未定,不敢援以为例耳。然亦当善处之,计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陈同父书云:“颜鲁子以纳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与之合耶?果若此爻,其於朱子何所当耶?幸教!
吏目邹立斋先生智读石翁诗
皇王帝伯一蒲团,落尽松花不下坛。岂是江山制夫子?祇缘夫子制江山。
乾坤谁执仲尼权,硬敢删从己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稳,不妨相过戊申前。(某录石翁诗,止得己酉年所作。)
御史陈时周先生茂烈陈茂烈字时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即有志圣贤之学,谓颜之克己,曾之日省,学之法也,作《省克录》以自考。登弘治丙辰进士第。奉使广东,受业白沙之门。白沙语以为学主静,退而与张东所论难,作《静思录》。授吉安推官,考绩过淮,寒无絮幕,受冻几殆。入为监察御史,袍服朴陋,蹩躠一牝马而自系,风纪之重,所过无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终养,给母之外,匡敝席,不办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闵其劳,遣二力助之。阅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送之还。日坐斗室,体验身心,随得随录,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诗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清苦,禄以晋江教谕,不受。又奏给月米,上言:“臣家素贫寒,食本俭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贫,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贫,非诚有及人之廉,尽己之孝也。古人行佣负米,皆以为亲,臣之贫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艰苦独至,臣虽勉心力未酬涓滴,且八十有六,来日无多,臣欲自尽尚恐不及,上烦官帑,心窃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谓:“时周平生履历之难,与己同而又过之。求之古人,如徐节孝者,真百炼金孝子也。”先生为诸生时,韩洪洞问莆人物于林俊,俊曰:“从吾。”从吾者,彭韶字也。又问,曰:“时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书生耶!”俊曰:“与时周语,沈顿去。”其为时所信如此。长史林缉熙先生光林光字缉熙,东莞人。成化乙酉举人。己丑会试入京,见白沙於神乐观,语大契,从归江门,筑室深山,往来问学者二十年。白沙称“其所见甚是超脱,甚是完全。盖自李大而外,无有过之者”。尝言:“所谓闻道者,在自得耳。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终是闲也。”甲辰复出会试,中乙榜,授平湖教谕。历兖州、严州府学教授,国子博士,襄府左长史。致仕。年八十一卒。
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贫就平湖谕。十年官满来归,母氏无恙。再如京师,将求近地养亲,未及陈情,遂转兖州。於是奏请改地,冢宰不许。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责其“因升斗之禄以求便养,无难处者,特於语默进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决,遂贻此悔,胸中不皎洁磊落也”。又言:“定山为窘所逼,无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几日求活,一齐误了也。”然则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许,况兖州乎?其许之也太过,故其责之也甚切耳。
长史林缉熙先生光记白沙语
先生初筑阳春台,日坐其中,用功或过,几致心病。后悟其非,且曰:“戒慎与恐惧,斯言未云偏。后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间。”盖验其弊而发也。
曾论明道论学数语精要,前儒谓其太广难入,歎曰:“谁家绣出鸳鸯谱,不把金鍼度与人。”
先生教人,其初必令静坐,以养其善端。尝曰:“人所以学者,欲闻道也,求之书籍而弗得,则求之吾心可也,恶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觑破,若觑不破,虽日从事於学,亦为人耳。斯理识得为己者信之,诗文末习,着述等路头,一齐塞断,一齐扫去,毋令半点芥蔕於胸中,然后善端可养,静可能也。始终一境,勿助勿忘,气象将日佳,造诣将日深,所谓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来也。”
州同陈秉常先生庸陈庸字秉常,南海人。举成化甲午科。游白沙之门,白沙示以自得之学,谓:“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张东所因先生以见白沙,有问东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诩。”年五十以荆门州同入仕。莅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门不入城郭。督学王弘欲见之,不可得。同门谢祐卒而贫,先生葬之。病革,设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李孔修字子长,号抱真子。居广州之高第街,混闤闠,张东所识之,弔入白沙门下。先生尝输粮於县,县令异其容止,问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与上官为礼。”复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无言而出。白沙诗“驴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谁?如何叉两手,刚被长官笞”所由作也。父殁,庶母出嫁,诬先生夺其产。县令鞫之,先生操笔置对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礼敬。诗字不蹈前人,自为户牖。白沙与之论诗,谓其具眼。尝有诗曰:“月明海上开樽酒,花影船头落钓簑。”白沙曰:“后廿年,恐子长无此句。”性爱山水,即见之图画,人争酬之。平居,管宁帽,朱子深衣,入夜不违。二十年不入城,儿童妇女皆称曰“子长先生”。间出门,则远近圜视,以为奇物。卒,无子,葬於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凿,相传不慧之事,世多附益之。或问:“子长废人,有诸?”陈庸曰:“子长诚废,则颜子诚愚。”霍韬曰:“白沙抗节振世之志,惟子长、张诩、谢祐不失。”
谢天锡先生祐
谢祐字天锡,南海人。白沙弟子。筑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袜不掩胫,名利之事,纤毫不能入也。尝寄甘泉诗云:“生从何处来,化从何处去。化化与生生,便是真元处。”卒后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诗,未免竟是禅学,与白沙有毫釐之差。
文学何时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时振,番禺人。为郡诸生。及师白沙,即弃举子业。学使胡荣挽之秋试,必不可。白沙诗云:“良友惠我书,书中竟何如?上言我所忧,下述君所趋。开缄读三四,亦足破烦污。丈夫立万仞,肯受寻尺拘?不见柴桑人,丐食能欢娱。孟轲走四方,从者数十车。出处固有间,谁能别贤愚?鄙夫患得失,较计於其初。高天与深渊,悬绝徒嗟吁!”
运使史惺堂先生桂芳史桂芳字景实,号惺堂,豫之番阳人。嘉靖癸丑进士。起家歙县令,徵为南京刑部主事,晋郎中。出知延平府,以忧归。再补汝宁,迁两浙盐运使以归。
先是,岭表邓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学授傅明应。先生读书鹿洞,傅一见奇之曰:“子无第豪举为,圣门有正学可勉也。”手书古格言以勗,先生戄然,向学之意自此始。其后交于近溪、天台。在歙,又与钱同文为寮,讲於学者日力。留都六载,时谭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轻信也。其学以知耻为端,以改过迁善为实,以亲师取友为佽助。若夫抉隐造微,则俟人之自得,不数数然也。天台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台以御史督学南畿,先生过之,卒然面质曰:“子将何先?”天台曰:“方今为此官者,优等多与贤书,便称良矣。”先生厉声曰:“不图子亦为此陋语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习,以称此官耶?”拂衣而起。天台有年家子,宜黜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脚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尔作面皮物耶?”天台行部,值母讳日,供张过华,先生过见之,勃然辞去,谓天台曰:“富贵果能移人,兄家风素朴,舍中所见,居然改观矣。”其直谅如此。天台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药也。胡庐山为正气散,罗近溪为越鞠丸,史惺堂为排毒散。”
先生在汝宁与诸生论学,诸生或谒归请益,即辍案牍对之,刺刺不休,谈毕珍重曰:“慎无弁髦吾言也。”激发属吏,言辞慷慨,遂平令故有贪名,闻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养父,先生躬拜其庐,民俗为之一变。其守延平,七日忧去,而尽革从前无名之费。若先生者,不徒讲之口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