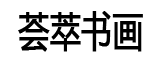劉向書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為「立」,如此字〔一〕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一〕姚本「字」,一本作「類」字。敘曰〔一〕: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行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二〕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三〕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
〔一〕姚本集,「曰」下有「夫」字。
〔二〕姚本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記本「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三〕姚本集作「朝會」。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一〕為侯〔二〕王;詐譎之國,興立〔三〕為強。是以傳〔四〕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五〕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六〕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七〕,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
〔一〕姚本錢、劉同。曾作「例」。
〔二〕札記今本誤重「侯」字。〔三〕姚本錢、集作「立」。曾作「兵」。〔四〕姚本一作「轉」。鮑本「傳」作「轉」。○
〔五〕鮑本「蓋」作「盡」。○
〔六〕姚本曾、集作「巧」。劉作「功」。〔七〕鮑本「不得施謀\,有設之強」作「不得施設,有謀\之強」。○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一〕,蘇秦結〔二〕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三〕,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四〕,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五〕之弊,終於〔六〕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七〕。」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一〕姚本集、曾無「弱」字。〔二〕姚本錢、劉,「結」下有「從」字。
〔三〕鮑本「固」作「國」。○〔四〕姚本一本下有「而」字。
〔五〕鮑本「謀\詐」作「詐謀\」。○
〔六〕鮑本「於」作「無」。○札記今本「於」作「無」。丕烈案:「無」字是也。
〔七〕札記今本「格」誤「假」。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一〕。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二〕教化,兵革〔三〕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一〕姚本脫字。
〔二〕鮑本無「國」字。○
〔三〕姚本錢,「革」下有「亦」字。
曾子固序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一〕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一〕鮑本「率」作「卒」。○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一〕。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一〕鮑本無「也」字。○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一〕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一〕鮑本「法」上有「為」字。○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一〕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一〕鮑本「不泯」兩字不重。○札記今本「不泯」兩字不重。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一〕
〔一〕札記今本在首,鮑本在劉向序錄下。吳氏識此序後云:「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后出。予見姚注凡兩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丕烈案:當在此與下李文叔諸跋連者為是。今本在首,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據吳氏云,知為姚氏一本,然亦非鮑本,尤誤。
孫元忠書閣〔一〕本戰國策後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二〕五十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最脫漏〔三〕,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孫元忠〔一〕札記今本「閣」誤「閤」。下同。吳引不誤。〔二〕札記今本「伯」作「百」。吳引作「百」。
〔三〕札記今本「漏」誤「誤」。吳引不誤。
孫元忠記劉原〔一〕父語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一〕札記今本「原」誤「元」。吳引不誤。姚宏題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
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愨,殊為疏略。後再扣〔一〕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