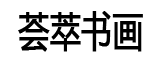延平元年(丙午、一0六)
春正月癸卯,光祿勳梁鮪為司徒。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順陵〔一〕。
〔一〕范書殤帝紀作「慎陵」。注曰:「俗本作「順」者,誤。」按劉攽東漢刊誤曰:「案皇后紀,和熹皇后葬順陵,以為皇后紀誤。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必不相襲。參校前後,孝和實葬順陵,言慎乃更為誤耳。」按御覽卷九一引東觀記正作「順陵」,范書及李賢注誤也。
初,賜周、馮貴人歸園。太后詔曰:「朕與貴人託配后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一〕,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典分歸外園〔二〕,相戀之情,感增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三〕?其賜貴人青蓋車,驂馬各一〔四〕,黃金四十斤〔五〕,雜綵三千匹。」
〔一〕李賢曰:「煢煢,孤特之貌也。詩曰「煢煢在疚」。」
〔二〕此句原作「貴人當以舊歸典分園外」,據范書和熹鄧皇后紀以正之。
〔三〕李賢曰:「詩邶鄘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其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
〔四〕鈕永建曰:「鄧皇后紀作「其賜貴人王青蓋車、採飾輅、驂馬各一駟」。攷王青蓋車見續漢輿服志,採飾輅未詳。輿服志云「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而已」。云「油畫」,云「畫輈」,疑即採飾輅。云「右騑而已」,見此車無左驂,故賜驂為殊禮。范書云各一駟者,兼王青蓋車驂車而言也。紀文脫誤,誼不可通。」
〔五〕范書皇后紀作「三十斤」。
初,和帝宮人吉成,成御者志恨成,乃為相人,書太后姓字埋之。事下掖庭考驗,皆以吉成所為。太后獨念吉成「我待之有恩,雖下賤猶人,託賴上在時,未嘗聞有惡言,今我遇過於平常,何緣生此,不合人情」。即自呼見,反復實劾,果其御者所為。
夏四月,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
初,騭與同郡袁良為布衣之交,及騭當路,欲延良共議世事,良謝而絕之。
司空陳寵薨。
寵字昭公,沛國〔洨〕(佼)人也〔一〕。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常誡子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案人也。」王莽之誅何武、鮑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二〕,吾可逝矣。」即乞骸骨。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咸三子皆在位〔三〕,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田,斂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寵父躬復以律令為廷尉監〔四〕。
〔一〕據范書、續漢郡國志改。
〔二〕出易繫辭下。疏曰:「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得待終其日。言赴幾之速也。」
〔三〕咸三子,參、豐、欽也。
〔四〕躬乃欽之子,建武初為廷尉左監。
寵少習家法,辟太尉鮑昱府〔一〕。是時三府掾屬以不肯親事為尚,專務交游。寵嘗以事君之義,當供所職,以佐政治,何得但出入養虛。故獨勤心於事,數為昱陳當世治化。昱高其能,使掌天下獄訟,所平決無不壓伏。寵以律訟多錯,不良吏得生因緣致〔輕〕重〔二〕,乃為撰科條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寵雖〔傳〕(傅)文法〔三〕,然兼通經籍,奏議溫邃,號為名相。子忠,字伯〔始〕〔四〕,傳家業,〔收〕才能甚有聲譽〔五〕。
〔一〕鈕永建曰:「陳寵傳「太尉」作「司徒」。按鮑永傳,永平十七年,昱代王敏為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是昱先為司徒,終於太尉。章懷注引東觀記云,時司徒辭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比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民訟也。攷陳寵傳,寵辟司徒鮑昱府,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據此則昱為司徒時所上辭訟比七卷、決事都目八卷,即陳寵所撰,昱之辟寵,其在司徒府無疑。紀文作太尉,誤。」〔二〕據東觀記、范書補。
〔三〕據黃本改。
〔四〕據范書補。
〔五〕據范書補。五月辛卯,大赦天下。壬辰,河東恒山崩〔一〕。
〔一〕續漢五行志與袁紀同,而范書殤帝紀作「垣山崩」。洪亮吉以為恒山在上曲陽,不屬河東,應如殤紀作「垣山」為是。其說是。按續漢郡國志,河東郡有垣縣,縣有王屋山。注引博物記曰:「山在東,狀如垣。」則垣山即垣縣王屋山。
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為司空。
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思惟愆失,深自克責。新遭大憂,接以未和,徹膳擯服,庶有益焉。其減太官、上方諸服御靡麗難成之物。」
丁卯,詔免掖庭宮人六百餘人皆為庶人。
尚敏上疏陳興廣學校曰〔一〕:「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弘,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示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二〕,各敘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睹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為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恒矣。」〔三〕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
〔一〕尚敏,范書無傳,不詳邑里生平,此疏僅見袁紀。
〔二〕范書儒林傳序曰:「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袁紀作「五人五經」當有脫誤。〔三〕見論語述而。
於是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一〕。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讚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二〕,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斯為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
〔一〕易繫辭曰:「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二〕元康、五鳳皆宣帝時年號,公元前六五年至前五四年間。漢書儒林傳曰:「初,書唯有歐陽,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
初,陳留李充三徵不至,由是徵充為博士,俄遷侍中。車騎將軍鄧騭屈己禮之〔一〕,嘗設酒饌,請充及朝大夫。酒酣,騭曰:「幸得託椒房,位上將,幕府初開,欲延天下英俊,君其未聞?」充曰:「將軍誠\能招延俊乂,以光本朝,不為難矣,但患不為耳!」因說海內隱士,頗不合,騭舉炙〔啖〕充曰〔二〕:「君宜及溫食之。」充受炙擲地曰:「說士之樂,甘於啖炙。」遂拂衣而出。侍中張孟諫曰〔三〕:「聞足下面折鄧將軍以讜言〔四〕,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子孫,誠\不為足下取此。」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志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五〕,何能為子孫計!」由是不為權貴所容,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三後為三老五更〔六〕,天子賜几杖,訪以國政。
〔一〕按范書此事系於永初二年十一月鄧騭任大將軍之後,時騭幕府初開,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此等與袁紀騭之語正合,疑袁紀置此誤。
〔二〕據范書補。
〔三〕范書李充傳作「汝南張孟舉」。
〔四〕讜言,說文曰:「直言也。」讜音黨。
〔五〕出詩邶風谷風。言自身尚且難保,何暇顧及子孫。
〔六〕范書李充傳作「年八十八」,惠棟引袁紀作「年八十四」,錄以存疑。
秋七月辛亥〔一〕,帝崩崇德殿。
〔一〕范書作「八月辛亥」,按七月丙子朔,不當有辛亥,當以范書為是。通鑑作「八月辛卯」,亦誤。初,清河王慶子祐〔一〕,生而有神光、赤蛇之異。年十歲善史書,善經傳。和帝甚器之,號〔曰諸生〕(日請)〔二〕,賞賜恩寵,異於諸子。和帝崩,殤帝在抱,太后詔留清河邸,以為儲副。及殤帝崩,群臣皆為屬意平原王勝。太后以前不立勝,恐為患,與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青蓋車以迎祐於清河邸〔三〕。〔一〕范書章帝八王傳與袁紀同,而安帝紀作「恭宗孝安皇帝諱祜」。東觀記、通鑑均作「祜」。惠棟引說文曰:「祜,上諱。」徐鉉云:「安帝名也。」則袁紀作「祐」,誤。今存其異文。
〔二〕據東觀記改補。〔三〕據范書補。
癸丑,立為長安侯〔一〕。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撫育幼帝,日月有望,遭家不造,仍罹凶禍。朕惟平原王素被錮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祐稟性忠孝,小心翼翼〔二〕,年已十三,嶷然有成人之體。禮:昆弟之子猶子也〔三〕。其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
〔一〕楊樹達曰:「宣帝將立,先封陽武侯,此用其故事也。」
〔二〕見詩大雅大明之章。
〔三〕見禮記檀弓上,「昆」作「兄」。
自延平初,鄧騭兄弟常在禁中,至是乃就第。
丙寅〔一〕,葬孝殤皇帝于康陵。
〔一〕範書作九月事。按九月乙亥朔,無丙寅,當以袁紀為是。己亥,隕石於陳留〔一〕。〔一〕範書作「乙亥」,是。疑袁紀上脫「九月」二字。
冬,西域諸國反。都護任尚上書求救。遣騎都尉班雄、校尉梁慬將五千人出塞〔一〕,會尚自疏勒還,與慬共保龜茲。溫宿、姑墨二國將數萬人圍慬,月餘,慬擊破之,斬首數萬級。道不通,慬遂留龜茲。〔一〕范書梁慬傳作「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按續漢百官志無西域副校尉一職。而漢書百官公卿表載西域都護屬官有副校尉一職,秩比二千石,官居元帝所置戊己校尉之上。然何以不見西域校尉一職?陳直先生漢書新證曰:「西域都護,有時稱為西域校尉。」居延漢簡釋文所載「鄯善以西校尉吉」,即西域都護鄭吉,故都護之外不另設校尉之職。東漢始建,無暇西顧,未設都護及其屬官。明帝永平十七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而未言及副校尉。按范書西域傳:「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可見已設副校尉一職,且系都護之主要助手。又竇憲傳載,和帝永元二年,憲曾遣副校尉閻槃擊伊吾。安帝永初初,詔罷西域都護,副校尉一職亦隨之取締。至元初六年,鄧太后詔許班勇所奏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事,其職始復立。據此袁紀「校尉梁慬」之上當脫「副」字。
初,西域自武帝時始通,三十六國其俗頗率著城郭田畜。地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十)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一〕。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渡)河〔二〕,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三〕,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而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四〕。
〔一〕據漢書西域傳改補,「東西六千餘里」下恐尚脫「南北千餘里」句。
〔二〕據南監本改,漢書西域傳作「波河」。波,循也,與陂通。
〔三〕據漢書西域傳補。〔四〕據王念孫說改。匈奴彊盛,常屬役匈奴。宣帝神雀中,漢置西域都護。王莽時,數遣五威德軍出西域〔一〕,車師諸國貧困,由是故叛。而(諸)都護李宗抄暴南道〔二〕,改其國號,以疏勒為世善,姑墨為積善,或易置王侯,於是西域與中國遂絕。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蔥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其事,或與前史異,然近以審矣。
〔一〕漢書西域傳、王莽傳均作「五威將王駿」。疑「德」系「將」之誤。〔二〕漢書西域傳「李宗」作「李崇」。「諸」字是衍文。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通伊吾(五)千里〔一〕。自伊吾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北通後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門也〔二〕。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葡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與匈奴爭車師、伊吾虛之地,以制西域。
〔一〕范書西域傳作「千餘里」,袁紀之「五」字乃涉上文「吾」字而衍,故刪。
〔二〕指後部之金滿城。又伊吾至前部高昌壁,范書作「千二百里」,袁紀恐脫之。
故自鄯善國治驩泥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此通車師前、後王及車且彌、旱陸、蒲類、〔移〕(條)支是為車師六國〔一〕,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二〕,後部西通烏孫。漢欲隔絕西域、匈奴,必得車師,屯田伊吾。
〔一〕車且彌,范書作「東且彌」,漢書分作「東且彌」、「西且彌」。旱陸,漢書作「卑陸」,范書與袁紀同。又條支遠在西海之濱,不當列入車師之國。范書作「移支」,故據以正。〔二〕據范書補。
焉耆治河南城〔一〕,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東南與山離國接,其餘危須、尉黎、龜茲、姑墨、溫宿、疏勒、休修〔二〕、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烏弋、罽賓、莎車、于闐、且〔末〕、〔拘〕彌〔三〕諸國轉相通。
〔一〕范書作「南河城」。沈家本後漢書瑣言曰:「前書治員渠城。按「南河」,漢書考證(齊召南)引此作「南柯」,未知所據何本。」
〔二〕黃本作「沭修」,漢書西域傳作「休循」。
〔三〕據范書西域傳補。
是秦為西域〔一〕,大月〔氏國治藍氏〕城〔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
〔一〕此句錯訛已甚,不解其意。〔二〕據范書西域傳補。
天竺,一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一〕。又有別城數十,置王〔二〕,而皆總名身毒。其俗修浮圖,道不伐殺,弱而畏戰。本傳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內眾數萬〔三〕,小國數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守其中,至東京時,〔詐〕(作)謀\茲生〔四〕,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五〕。〔一〕范書西域傳「盤越國」作「磐起國」。鈕永建曰:「攷太平御覽四夷部有磐越國,引魏書云在天竺東南數千里。又梁書海南諸國傳云: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從月氏、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越云云。此文正用後書語,亦作磐越,則范書作「磐起」蓋誤,當以袁紀正。」
〔二〕范書作「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袁紀當有脫誤。〔三〕內與眾原倒置,逕正之。
〔四〕詐作形近而訛,故正之。〔五〕以上所謂本傳語乃東觀記西域傳之文。四庫館臣輯東觀記,亦失錄。
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地方數〔千里〕(百)〔一〕。西至條支,馬行六〔十〕(千)日,臨〔西〕海〔二〕。暑熱卑濕,出師子、犀牛、犎牛,孔雀卵大如瓮。(與西海接)〔三〕自安息西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三千六百里〕〔四〕。渡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五〕。其南乘海,乃通大秦,或數月云。
〔一〕范書西域傳作「地方數千里」,袁紀誤「千」為「百」,下又脫「里」,皆正之。
〔二〕據范書改補。
〔三〕此乃衍文,刪。
〔四〕依上下文例,據范書補。
〔五〕據范書補。
大秦國,一名黎軒〔一〕,在海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海〕(漢)廣大〔二〕,水鹹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歲〔三〕。故入海者皆賚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土俗。
〔一〕班書作「犁靬」,范書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