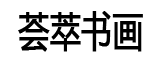萧韩家奴李汗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搜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
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搏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鉴经史,通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始仕。
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直取牛。二十八年,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迁天成军节度使,徙彰愍宫使。帝与语,才之,命为诗友。尝从容问曰:“卿居外有异闻乎?”韩家奴对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盖尝掌栗园,故托栗以讽谏。帝大笑。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徭役不加于旧,征伐办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廪既实,而民重困,岂为吏者慢、为民者惰欤?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
补役之法何可以复?盗贼之害何可以止?”韩家奴对曰: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绿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
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臣谓不然。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对此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可敦,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领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胜言者。况边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顿绝。得不为益,舍不为损。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卒难赴援。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弃地则损威。殊不知殚费竭财,以贪无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国,万一有败,损威岂浅?或又云,沃壤不可遽弃。臣以为土虽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敌来,则不免内徙,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
夫币禀虽随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济天下。如欲均济天下,则当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
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
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边戍兵亦然。譬如一功之土,岂能填寻丈之壑!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
臣又闻,自背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今宣徙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罢黑岭二军,并开、保州,皆隶东京;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候尉相望,缮完楼橹,浚治城隍,以为边防。此方今之急务也,愿陛下裁之。
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自是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
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醻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讽。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
臣以为三皇礼文末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背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迫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
疏奏,帝纳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见帝猎,末尝不谏。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
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响化,然礼书末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商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时帝以其老,不任朝谒,拜归德军节度使。以善治闻。帝遣使问劳,韩家奴表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汗,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当太宗崩、世宗立,恟不定,汗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久之,从归上京,授翰林学士。
穆宗即位,累迁工部侍郎。时汗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密遣人召汗。汗得书,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汗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汗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观致罪。且汗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
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汗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
论曰:“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策,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李汗虽以词章见称,而其进退不足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