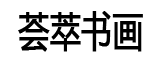忠信是以忠对信而论,忠恕又是以忠对恕而论。伊川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是就心说,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字义中心为忠,是尽己之中心无不实,故为忠。如心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就一边论。其实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须要施于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达,人亦欲达,必欲推己之欲立、欲达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达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门之内,应接无几,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则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广。茍中天下而立,则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养其亲,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冻饿,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长吾长、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离散,不得以安其处;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内困穷无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乐。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两片则为二物。上蔡谓:忠恕犹形影。说得好。盖存诸中者既忠,则发出外来便是恕。应事接物处不恕,则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实。故发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圣人分上,则日用千条万绪,只是一个浑沦真实底流行去贯注他,更下不得一个推字。曾子谓“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学者工夫上二字来形容圣人一贯之旨,使人易晓而已。如木桹上一个生意是忠,则是这一个生意流行贯注于千枝万蕊底便是恕。若以忠恕并论,则只到那地头定处,枝成枝、蕊成蕊,便是恕。大概忠恕本只是学者工夫事。程子谓“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天岂能尽己推己,此只是广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维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复元,万古循环,无一息之停,只是一个真实无妄道理。而万物各具此以生,洪纤高下,各正其所赋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圣人,也只是此心中一个浑沦大本流行泛应,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当止之所,此是圣人之忠恕也。圣人之忠便是诚,更不待尽。圣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无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著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是也。有圣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贯之是也。有学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圣人本无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何待于推?学者未免有私意锢于其中,视物未能无尔汝之间,须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这物上。既推得去,则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贡问: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盖学者须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仁可得矣。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单言恕,则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无忠,则从何物推去?无忠而恕。便流为姑息。而非所谓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学者之忠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说圣人之忠恕。圣人忠恕是天道,学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语子贡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是中庸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异时子贡又曰“我不欲人之加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亦即是此意,似无异旨。而夫子乃以为“赐也,非尔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盖是亦理一而分殊。曰“无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
自汉以来,恕字义甚不明,至有谓“善恕己量主”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谓“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据他说,恕字只似个饶人底意,如此则是己有过且自恕己,人有过又并恕人,是相率为不肖之归,岂古人推己如心之义乎?故忠宣公谓“以责人之心责己”一句说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说得不是。其所谓恕,恰似今人说“且恕”、“不轻恕”之意。字义不明,为害非轻。